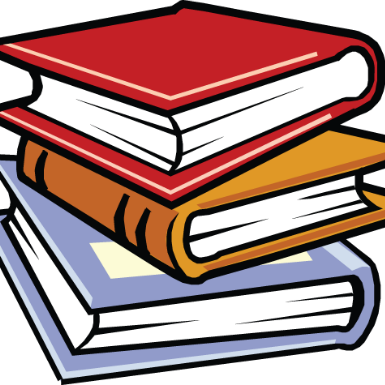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並沒有解決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矛盾。戰爭的創傷在歐洲尤為突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60年代初,德國、法國和整個歐洲都始終沒有從戰爭恐怖、經濟危機和社會道德敗壞的氣氛中擺脫出來。一部分人懷著美麗的憧憬嚮往和平的到來,希望和平可以給社會帶來安寧和幸福。但是,殘酷的事實——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爾及利亞戰爭以及接二連三的經濟動盪和蕭條等等,使某些人的善良願望破滅了。在戰後的歐洲,特別是法國、義大利、德國,悲觀、失去信心、互不信任的心理很普遍。在這種情況下,存在主義哲學,特別是薩特的存在主義就像瘟疫一樣迅速地傳播開來。
如果說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反映了壟斷資本階級狂妄、孤注一擲的世界觀的話,那麼,薩特的存在主義就比較典型地反映了對生活不抱希望,然而充滿著空洞的個人幻想的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在戰爭、失業、通貨膨脹和社會墮落的打擊下,小資產階級忽而悲觀失望、生活無著落、絕望到極點,忽而想入非非,充滿著幻想,狂熱到極點。所有這些,在薩特的著作中都得到了最生動的描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短短的10年,薩特因寫出存在主義的哲學和文學著作成為舉世聞名的哲學和文學家。在薩特的周圍,也興起了一批有影響的人物:馬塞爾、加繆、梅洛-龐蒂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等人。
存在主義迅速地越出了德國和法國的國界,在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等國蔓延開來。連一向在思想傳統上比較保守的英國也出現了存在主義的狂熱信徒。英國著名的劇作家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和蘇格蘭心理學家羅納德·萊英(Ronald Laing,1927-1989)是在英國宣傳存在主義的主要人物。
20世紀50年代,存在主義哲學越過大西洋傳到了美國。當時,薩特的《無出路》(No Exit)和《蒼蠅》以及加繆的《異鄉人》等劇本首先在紐約上演,並迅速地在美國各地掀起一股推崇存在主義的狂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世界中漫延著的悲觀、失望和彷徨的思想情緒,也同時反映在當時的文學、史學、宗教界當中。
20世紀50年代英國興起的「憤怒的青年」(The Angry Young Men)與發端於美國、後來又流行於歐洲各國的所謂「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和「嬉皮士運動」(Hippies)等,都是和存在主義一樣的社會現象。英國屬於「憤怒的青年」的女作家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1919-2013)說:「當今之世,是一個十分危險的時代,世界上誰都給恐懼和不安弄得六神無主了……目前要分辨好與壞都很困難……我只有迫使自己幻想該怎樣活下去。」與萊辛一起的科林·威爾遜(Colin Wilson,1931-2013)在他所寫的《局外人》一書中,甚至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存在主義的宗教」作為根治當前社會弊病的藥方。
英國的這些「憤怒的青年」,大都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們都經歷過戰爭的嚴酷考驗。他們對戰爭的殘酷性記憶猶新。在他們看來,生活就像一場惡夢。戰後的動盪不安又使他們感到困擾,他們感到生活既無意義又無目的,到處都碰上「此路不通」的牌子,因此,他們不僅感到自身前途茫茫,連自己的國家、社會以及整個人類究竟會往何處去,也無從瞭解。因此,他們整日在沮喪、彷徨中,在無聊的「個人刺激」中度過。
同在歐洲一樣,美國的「垮掉的一代」是一群悲觀厭世、狂妄蠻幹的青年。他們的作品、行為,同存在主義所主張的人生觀一脈相承。他們否定一切,厭恨一切,只有自己的存在才是至高無上的。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們的憤世嫉俗使他們厭惡清醒,他們的自我擴張使他們否定一切客觀存在。於是他們酗酒、吸毒、賭博、在高速公路上駕車橫衝直撞,讓自己永遠處在半昏迷的狀態;在狂熱的爵士音樂的伴奏下瘋狂地跳搖擺舞;他們亂搞男女關係,尋找「性刺激」。他們認為,人的最正常狀態就是失去理性。因此,他們幻想自己是瘋子,有的也真的成了瘋子。他們在美國丹佛一個廁所的牆上,寫道:「如果你熱愛生活,可恥便是你的名字。」他們老是嚷著要自殺,真正自殺的卻不多。在美國,這些「垮掉分子」(Beatnik)越來越多。美國的耶魯大學裡,這些垮掉分子經常聚集在斯特林紀念圖書館地下室的廁所裡開會。廁所是他們最喜歡的地點。在他們的心目中,世界已到了末日階段,全人類都瀕臨死亡,他們既否定過去,又否定未來,只有眼前的存在才是靠得住,而眼前的存在中,唯一確實存在的就是「自我」。
所有這些反映在文學界和社會生活中的頹廢厭世人生觀,都是存在主義哲學的孿生兄弟。他們都有同樣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當我們巡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至20世紀60年代的歐美社會生活和人的整個思想面貌和精神狀態以後,我們再回過頭來認識存在主義氾濫的社會現象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存在主義似乎不像20世紀50年代那樣為人們所傳頌。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在實際上,由於產生和滋長存在主義的社會條件並沒有消除,存在主義思想的幽靈仍然遊蕩在歐美各國的社會上。人們在口頭上不再更多地談論存在主義,只是因為追求時髦的西方人不願意連續十年以上一直重複著同樣的存在主義概念。他們熱衷於用新的概念代替舊概念。但是這些名稱卻裝載著同樣內容的思想。更何況存在主義經過十多年的傳播已經在相當多的歐美人當中留下較深的印象。所以,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相當多並不自稱為存在主義者的歐美人士,特別是青年一代,實際上仍以存在主義人生觀作為他們行事處世的指導思想。美國電影《毛髮》很生動地反映了這個事實。
美國的「嬉皮士運動」、「耶穌運動」(Jesus Movement)等等就是其中的典型。
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和歐洲社會及世界局勢是與20世紀50年代有所不同。科學技術的發展並未能消除社會的不平等。相反,舊的問題未了,新的問題接踵而至。失業、物價飛漲、越戰升級、世界局勢的動盪不安,使歐美許多人不能不為自己和世界的未來而擔憂。悲觀厭世已不是一部分人的奢侈品,而變成許多人的必需品了。所以,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仍然是不可忽視的。
存在主義也和歐美其他流行的哲學流派一樣,在其發展過程中,往往要經歷各種變化。20世紀60年代後的存在主義不僅在傳播的廣度上有新變化,而且,存在主義本身也正發生變化,存在主義信奉者的隊伍分化是顯著的。
就連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海德格爾和薩特,也從20世紀60年代末以後,不再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存在主義的某些思想,也正演變成其他的更加「時髦」的哲學流派。
住在香港地區的中國人要理解當代存在主義所鼓吹的那種思想是不難的。因為目前的香港社會也到處顯示出存在主義所鼓吹的恐懼、絕望、冒險、賭注、以自我為中心、反理性等思潮和情調。在香港的電影院裡,每天可以看到以「世界末日」、頹廢、厭世、狂妄、縱慾等內容為主題的影片。1978年9月,筆者觀看名為《刀女》的影片。片中的一群女青年每天過著酗酒、兇殺、鬥毆、搶劫的生活,她們沒有理想,能過一天就算一天;她們目中無人,只相信自己的意志;她們想怎樣「存在」,就怎樣「存在」。影片最後以「蕩婦黨」頭目的狂叫結束。這一影片難道不是存在主義的最好寫照嗎?
綜上所述,存在主義直到今天仍在影響著社會生活。
目前,存在主義主要可分為三大派別:
1.以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這一派存在主義者比較接近中下層群眾,具有較多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對社會的不滿。但他們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只能從個人求解脫中尋找出路,因此,他們只看到自己,不相信自己。
2.以雅斯貝爾斯、馬塞爾為代表的存在主義;這一派人都是基督教的信仰主義者。他們在否定生活、否定社會之後,把目光轉向天國,祈禱於上帝的存在。
3.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存在主義;這一派人因德國在二次大戰的慘敗而悲觀失望,轉向隱居生活,企圖逃避現實。這一傾向,反映在他們的著作中,就表現出更多的抽像的思辨。他們的著作,越到晚期,越玩弄抽像、晦澀的哲學概念。他們的存在主義哲學到後來,越局限在少數哲學家和追隨他們的青年學生的小圈子裡。1976年,海德格爾去世後,這一派存在主義者面臨著分崩離析的邊緣。
但是,海德格爾的逝世,一點也不意味著存在主義思想的消亡。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一方面,海德格爾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陸續發表的新著作,特別是有關批判形而上學和有關語言以及有關藝術的著作,仍然產生越來越深廣的影響;另一方面,他的學派慢慢地演變成各種新的思潮:從20世紀60年代以後,深受海德格爾思想影響而在近30年來的西方思想領域內佔據重要地位的新派別,包括:以伽達默爾為代表的存在主義哲學詮釋學、以德裡達為代表的「解構學派」、以福柯為代表的「後結構主義」以及以李歐塔為代表的「後現代派」等。此外,在哲學思想領域之外,海德格爾的思想也深深地影響著文學藝術界和美學界以及神學理論界。
海德格爾對於20世紀60年代後的思想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致有人承認一種「後海德格爾主義」的時代的到來——這個「後海德格爾主義」的主要特點,是以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詮釋學、語言理論、科學技術理論及對舊形而上學的批判思想為基礎,或多或少地吸收尼采主義、結構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及象徵主義等各種派別的思想觀點和方法,集中地批判傳統西方文化、道德和藝術,提出了「重新建構」適應於「後現代性」社會的嶄新文化的宏大而又有點含糊不清的目標。
海德格爾同薩特一起,一直以其深刻思想,影響著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的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發展。在20世紀60年代後發表的海德格爾著作,包括:《尼采》兩卷本(Nietzsche,2 Bde.,1961)、《關於物的問題》(Die Frage nach dem Ding,1962)、《技術與轉向》(Die Technik und die Kehre,1962)、《路標》、《藝術與空間》、《論思想之物》(Zur Sache des Denkens,1969)、《現象學與神學》、《赫拉克利特》(Heraklit,與歐根·芬克〔Eugen Fink〕合著,1970)、《謝林論人的自由的本質》(Schellings Abhandlung ue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1971)、《早期作品集》及《邏輯學》等。這些著作都是在人們所謂「存在主義過了時」的時代中出版的,但由於這些著作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它們不僅對存在主義本身,而且也對其他哲學派別及對其他人文學科發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所以,海德格爾的思想在20世紀60年代後不但沒有「過時」,反而在西方思想界刮起了一股研究熱潮,方興未艾。
薩特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也同樣地不斷發表新著作,繼續擴大他的存在主義的影響。
海德格爾和薩特等人的存在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後的繼續發展,表現了存在主義的極其複雜而深刻的成熟形態,也表現了它對西方哲學和人文科學的新發展所作出的特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