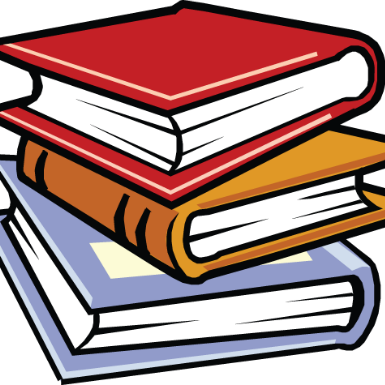在制度性作惡的脅迫力量左右著幾乎每個人思想和行為的社會裡,個人良心往往就會被看成是一種可能的抵抗力量,人心、人性的心智覺醒也就越加顯得重要。在這樣的社會裡,人的心智覺醒難度要比在一般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大得多。這一心智覺醒可能會產生兩個問題:人的良心是與生俱來的嗎?對人的行為,個人良心向善的引導總是與主導社會的價值觀相一致嗎?
美國作家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在《瓦爾登湖》(Walden,1854)的第十八章中寫道:“如果一個人與他的同伴步伐不合,那也許是聽到了一個不同的鼓聲。不管這是怎樣的鼓聲,來自多麼遙遠的地方,他都會隨著那音樂聲前行。”梭羅是一個聽自己良心鼓聲行進的人,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崇尚人類單純的心靈,認為生活越簡單,宇宙的規律也就越簡單。他的個人良心讓他在眾人皆醉的時候擁有獨自的清醒,像一個獨善的隱士那樣不受喧囂紛雜社會的攪擾。梭羅是一個寂寞的人,他的書打動一些與他一樣在心底深處寂寞的讀者,但他的良心鼓聲卻並不能喚起他們與他一起前行。連他的一個朋友都說:“我愛亨利,但無法喜歡他,我決不會想到挽著他的手臂,正如我決不會想去挽著一棵榆樹的樹枝一樣。”
我們要傾聽的是另一種良心鼓聲,一種能讓我們與他人同行的良心鼓聲。這個鼓聲來自每個人的內心,但它並不孤獨寂寞,因為我們能夠互相聽到來自他人的心靈迴響。即使暫時聽不到迴響,也不等於沒有迴響,因為這迴響就像是樹林子裡的回聲,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從某個並不期待的方向突然聽到了它。當這聲音響起的時候,如加繆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所說,它“會使一切偶像都沉默下來。宇宙突然恢復了它的沉靜,大地上無數詫異的小小的聲音就會升起。……秘密的呼喚,從所有的臉上發出邀請”。回聲一旦響起,你會感覺到這是朝你而來。這個回聲來自人們在社會中為共同的善而不斷進行的心智交流,人心和人性的啟蒙就是為了促進這種心智交流,並加入這個交流。
公民啟蒙和心智啟蒙
良心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類用理智,而不是僅僅依靠直覺或本能來做的善惡、對錯、是非判斷,並因此有所行動。良心不只是人有什麼情感、情緒或想法,而是有與此相應的行為。沒有行為和行動的良心只是空洞、模糊、曖昧的心理衝動,也會因此變得萎靡衰竭。和美德一樣,良心是某種我們需要用行動來養育的東西,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我們是因為行正義之事才變得正義的,是因為有所節制才有節制的,是因為做勇敢的事才成為勇敢的”。同樣,良心也是某種要麼運用,要麼失去的東西。如果說良心因自由而彌足珍貴(保護“良心自由”的理由),那麼,良心的自由只能在行動中才能得以實現。
康德把自由當作評判人性善惡的前提,他區分了人的自然本性和道德本性,認為自然本性無所謂善惡,因此把人的自然本性從善惡論中排除出去。雖然“人性”具有自然人性和道德人性的廣泛內涵,但是,就改良道德、砥礪品行而言,人的向善或不向善,墮落與不墮落實際所指的是人心,而不是人性,因此人性是本惡、本善,還是兼而有之,則不需要在這裡成為主要的問題。
我們關注的是人的自由本性,也就是可以作出自由道德選擇的人心。按照康德的說法,它首先在人的內心意念層面上展開行動,然後才貫徹和實施到外顯的經驗行動中。具有道德善惡意義的人性其實就是人心,而人性的善惡則是人心的好歹,即良心和歹心。因此,對人性善惡的事實層面上的判斷,也就是對於人在動機和行為的一致性上的善與不善的區分。我們常常在正面的意義上運用“人心”這個說法,特指善良的心地、良心,其反面即為“歹心”或“沒良心”(也就是“人心敗壞”)。以人的自由本性和自由心智為出發點的人心啟蒙與公民知識啟蒙有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讓盡量多的普通人,而不是少數聖賢或精英,能夠共同建立起一種訴諸自由而非壓制、共好而非獨善、德行而非強權、民主而非專制的好的公共生活。啟蒙不是行為指導,而是心靈開啟,不只是糾錯,而且更是教育。英國教育思想家亨利·皮查姆(Henry Peacham,1546—1634)說,“不含教育的糾正是平庸的虐政”,心智啟蒙便是要用養育人心來化弭這樣的虐政。
一百多年前,梁啟超寫《新民說》啟蒙國人,倡導“開民智”和“新民德”。在《新民說·論私德》中,他把中國人的“私德墮落”歸結為五個原因,四個是腐蝕的原因,一個是疏忽的原因。腐蝕的原因是專制、暴君、戰亂、貧困,疏忽的原因是讀書人的“學術匡救之無力”。就像梁啟超把“公德”和“私德”分開來討論一樣,我們可以把政治的公民知識啟蒙與人心的心智啟蒙分開來進行,梁啟超所說的“私德墮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我們今天心智啟蒙和改良人心所最關心的。心智啟蒙是政治啟蒙的基礎,也是政治啟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所包含的理性和智識使得它必然把注意力投向“心智”意義上的人心。
梁啟超在《新民說·論私德》中總結中國人“私德墮落”的原因,其中有兩條與政治制度有關,一條是“專制政體之陶鑄”。專制制度對人民的道德敗壞是一種政體對人格的摧殘,古今如此,中外皆然。他引用孟德斯鳩的話說:“凡專制之國,間或有賢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則甚希。試征諸歷史,乃君主之國,其號稱大臣近臣者,大率畢庸劣卑屈嫉妒陰險之人,此古今東西之所同也。不寧唯是,苟在上者多行不義,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貴族專尚詐虞,而平民獨崇廉恥,則下民將益為官長所欺詐所魚肉矣。故專制之國。無論上下貴賤,一皆以變詐傾巧相遇,蓋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
另一條是“由於近代霸者之摧鋤”,也就是“英明”君主和領袖在“太平盛世”對人民思想所作的有效鉗制。以清代的“雍乾盛世”為例:“及夫雍、乾,主權者以悍鷙陰險之奇才,行操縱馴擾之妙術,摭拾文字小故以興冤獄,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恥,……自魏武以後,未有敢明目張膽變亂黑白如斯其甚者也。”中國人民德的低下,如梁啟超所言:“前所播之惡果,今正榮滋稔熟,而我民族方刈之,其穢德之夐千古而絕五洲,豈偶然哉!豈偶然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詐偽”和“卑屈”這兩種道德墮落惡疾便是自然的收穫:“生息於專制空氣之下,苟欲進取,必以詐偽;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於此兩種性質之人,即其在社會上佔最優勝之位置者也。”
梁啟超把倡導私德和開啟公德一起作為開啟民智和現代國民教育的主要內容。一直到今天,公德與私德仍然是啟蒙的兩個重要方面。在梁啟超的時代,他發現中國人最欠缺的,不是個人與個人的倫理道德(如君臣、父子、兄弟、親戚、朋友之間),而是有關個人與國家關係的“民德”。雖然他傾向於把“民德”當作“公德”,但由於他對“私德”同樣重視,我們不妨把完整的民德視為公德和私德相互結合和缺一不可的產物。二者都是價值觀,前者是關於群體的,後者是關於個人的。正如梁啟超所說,“私德與公德,非對待之名詞,而相屬之名詞也”。天天提倡公德,今天五講四美,明天八榮八恥,學雷鋒、學模範,如果沒有私德就未必會有成效,比如,愛國為“公德”的第一要求,但愛國有誠有偽,有人把愛國變為口頭禪,以愛國為名行其自私自利之實,這是虛偽和不誠。虛偽和不誠就是私德的缺失。
因此,梁啟超說:“是故欲鑄國民,必以培養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欲從事於鑄國民者,必以自培養其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他又說:“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謬托公德,則並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養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過半焉矣。”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有良好的私德,如誠實(說真話)、勇敢(敢說真話)、有正義感(敢於在需要時站出來說話),那麼,只要他知道了做公民的道理(公民權利、義務、積極參與),就能夠成為一個好公民;而如果一味強調某種“公德”,如愛國、守法、納稅,乃至信仰某某主義、堅持什麼路線,那麼就可能滿口愛國為民,卻把“陰險反覆,奸黠涼薄”當作手段;或者出於私心和私利,拿“公德”來做統治別人的借口,根本就是“謬托公德”,這樣的人其實是什麼道德都沒有的。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公德的啟蒙主要是公民知識和道理的啟蒙,為的是瞭解公共生活需要怎樣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又應當如此才能擔任公民角色和參與民主生活。而私德的啟蒙則關係到心智的啟蒙,不僅需要知道人性中的“惡”和“苦”,如基督教所說的“原罪”、“七宗罪”和佛教的“苦諦”;還需要知道人心裡可能有哪些雖然自然,但卻不良的幽暗意識,如愚蠢、貪婪、狡詐、凶狠、陰險、淫亂、妒忌、作秀、勢利、偽善、輕信、偏執。當然也還要知道人可能有哪些雖然平常,但卻有害的行為傾向,如隨大流、騎牆觀望、首鼠兩端、盲目服從、盼望奇跡、做爛好人、別人鼓掌我也鼓掌、將別人非人化,等等。不良私德常常也叫作“心術不正”或“壞良心”,在私人和群體生活中都是有害的,有的是損人利己,有的是損人不利己。心智啟蒙是一種知識的啟蒙,不是類似宗教、靈修、養心、參悟的“心靈開啟”。它的作用並不體現在依靠某種神秘的力量,突然喚醒了人們的善惡直覺或道德頓悟,而在於讓盡量多的人看到,無論是旨在健全心智的人心啟蒙,還是準備民主政治的公民啟蒙,都是像康德所說的那樣,“公眾要啟蒙自己,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許他們自由,這啟蒙便是不可避免的”。
心智啟蒙的內容
人性和人心可以合稱為“人的本性”(human nature),心智啟蒙是為了幫助人們認識自己的本性,明瞭哪些是“人的本性中出錯的地方”。17世紀英國教育思想家讓·蓋拉德(Jean Gailhard)把釐清“人的本性中出錯的地方”當作人的教育和匡正人性的根本。他說:“要改成我們所需要的本性,只有經由教育的改造。”因此,教育也被稱為人的“第二天性”,教育造成人與人之間近於本性的差異,由於教育的不同,有的人顯得“天性善良”,有的人則顯得“天性邪惡”,這裡所說的天性,往往既指人性,也指人心。
心智啟蒙相信人的本性是可以改變的。人性和人心互相聯繫,但互有區別。人性中的“出錯”往往被稱為“惡”或“罪”,如基督教的原罪和七宗罪,而人心中的“出錯”則往往被稱作為“不良品質”。人性是道德神學的內容,人性中的“惡”或“罪”,其對立面是“善”,基督教認為上帝是善的化身,人要從善、克惡,就必須信仰上帝。與人性不同,人心首先是倫理、道德哲學、政治哲學、教育學的內容,後來又成為現代道德進化論和遺傳心理學的內容。人心的出錯是由於人的“自然癖性”,是可以通過人自己的教育、學習、訓練、習慣培養來得到約束和加以改變的。人可以借助自己的,而不是神的力量,在自然傾向的範圍內控制自己的行為。
在人文主義思考中,人性和人心則往往是交織在一起。例如,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說,人類心靈既是偉大的又是可悲的,“人是怎麼樣的虛幻啊!是怎麼樣的奇特、怎麼樣的怪異、怎麼樣的混亂、怎麼樣的一個矛盾主體、怎樣的奇觀啊,既是一切事物的審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材;既是真理的儲藏所,又是不確定與錯誤的淵藪,是宇宙的光榮而兼垃圾”,“人要求偉大,而又看到自己渺小;他要求幸福,而又看到自己可悲;他要求完美,而又看到自己充滿著缺陷;他要求能成為別人愛慕與尊崇的對象,而又看到自己的缺點只配別人的憎惡與鄙視”。使人過多地看到他與禽獸相似,而不向他指明人的偉大,那是危險的。然而,使人過多地看到自己的偉大,而看不到自己的卑鄙,那也是危險的。
人的多種多樣“不良品質”的對面是同樣多種多樣的“好品質”。英國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的《教育片論》就可以說是為糾正不良品質,培養好品質而寫的。正因為如此,個人品質與他在《政府論》中的政治哲學思考連為一體。《教育片論》的兩位編輯者(John W.和S. Yolton)在“引言”中對此寫道:“《教育片論》為道德個體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訓練和教育的方案,《政府論》則將這一個體投入到政治的競技場。……洛克在《教育片論》中所頌揚的德行既包括一些個人傾向的品性(如勤勞、謹慎),也包括一些社會美德(如仁慈、慷慨、有禮)。其哲學中的個人主義成分因他的兩個觀念——人類共同體和市民政治,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平衡。個體作為一種道德存在同時隸屬於這兩個共同體;而這兩個共同體則為洛克的道德設立標準,並保存其價值。”
《教育片論》討論的“不良品質”包括吹毛求疵、挑剔、笨拙的羞怯、輕蔑、貪婪、野蠻、跋扈、輕率判斷、偽善、怠惰、說謊、心懷惡意、粗心大意、魯莽、怯弱害羞、頑固、膽小,等等;而“優良品質”則包括彬彬有禮、仁愛之心、慷慨大方、榮譽、謙遜、勤奮、仁慈、愛學習、謙虛、有禮貌、謹慎、敬畏之心、自我控制、自我克制、自我抑制,等等。為不同的品格提供某種“德行的清單”,對於心智啟蒙不失為一種便利可行的方法。首先,它的內容是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其次,它教我們學會理解人,因為它教會我們通過對人的具體品格的定義、特徵和性質來取得對它們的認識,並促使我們依據在這些知識基礎上的合理判斷來有所行動,或對自己有所節制。
心智啟蒙既包括個人的道德教養內容,也包括公民的社會美德內容,而重點則更傾向於前者。一個多世紀前,梁啟超在中國環境中將道德分為公德、私德兩個範疇,公德是指那些促進群體凝聚力的道德價值觀;私德是指有助於個人道德完善的那些道德價值觀。對一個群體的凝聚力來說,最必不可少的自然是公德,但私德也十分重要,因為一個群體的總體素質最終取決於該群體個體成員的素質。因此,梁啟超認為私德絕非只是個人問題,它的首要價值乃在於有助於群體的集體利益。
今天,公德、私德的區別仍然存在,但已經不需要那麼強調,因為今天人們對於梁啟超所關心的“群”已經有了與他非常不同的理解和認識。由於民主思想的傳播,今天的人們大多把個人首先當作公民,而不只是國家的一分子,“公民”這個人格需要有一種比“國民”的民德結合得更緊密的公德和私德。20世紀的極權統治讓人們對“民德”的政治內容有了更充分、更清醒的認識,因為無數的事例讓他們看到,私德也許並無太大瑕疵的個人完全可能像納粹分子艾克曼那樣成為制度性作惡的工具,體現在艾克曼身上的那種分裂的“民德”是非常可怕的。
今天的心智啟蒙有了與梁啟超時代不同的宗旨,它是民主的,不是國家主義的,也就是說,它不只是為了造就能增強群體凝聚力的個人道德素質,而且更是為了造就一種能增強與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相一致的公民個體道德素質。只有這樣的公民個體道德素質才有助於促進民主群體的凝聚力,也才是心智啟蒙的現階段目標。
啟蒙的目標必然反映在啟蒙所提供的知識上,不同目標的啟蒙一定會對啟蒙者的知識和學問提出不同的要求。清代思想家黃宗羲說:“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又說:“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梁啟超對此說深表贊同,他說:“此誠示學者以求道不二法門哉!夫既曰各人自用得著,則亦聽各人之自為擇。”也就是說,一個人做學問並不是單純的積累“知識”,啟蒙也不是單純地把這樣積累的知識寫成文章告訴別人。啟蒙需要知道為什麼目標而啟蒙,啟蒙者的知識是為這個目標而服務的。啟蒙的目標是一種對特定社會、政治生態下現實需要的判斷結果。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梁啟超時代的中國,以今天中國的情況來看,人性、人心的啟蒙與公民知識的啟蒙具有相同的目標,那就是為在中國形成公民社會和民主生活秩序做一些必要的準備,這也是聽良心的鼓聲要走的路。
聽良心的鼓聲能走多遠
聽良心的鼓聲與他人同行,在這樣的結伴同行中,“能走多遠”取決於朝著什麼目標和有怎樣的行為。許多人因為身處極端的環境中,而不能有與良心的內在導向相一致的行為,他們的行為變得與良心無關或相背離。阿倫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和《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對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有過經典的政治道德分析,而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對權威的服從實驗”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則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許多不做好事或者做壞事和作惡的人,不是由於“良心泯滅”或是“沒有良心”,而是因為存在著遠比良心更強大的左右他們行為的力量和權威。因此,心智啟蒙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幫助人們瞭解這些權威及其力量的行使方式,讓他們知道人為何會“不由自主”地服從這些力量,這種服從又具有怎樣的心理和認知特徵。
人們在外力限制、思想操控、威權統治面前,能否擁有抵抗的意願和行動的能力,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對自己心智的認識。統治權力對人們的操縱、愚弄、宣傳洗腦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利用了人們自身的性格缺陷和心理弱點。人自身的性格缺陷和心理弱點,以及對自己情緒、慾望的無知為統治權力的操控提供了機會,也創造了條件,而統治權力的操控則又使得受害者更加難以擺脫自身的限制。因此,心智啟蒙必須針對人自身的愚蠢、冷漠、軟弱和懈怠。我們需要承認人性中有惡的積習,對之保持足夠的警惕,並知道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克服這些傾向。心智啟蒙必須在認識和改造這些惡的積習中完成。社會的進步取決於人類不斷努力去消除人心改進與自然傾向的對立,這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可以獨自完成的。人心和良心的社會性決定了個人只有與他人一起,聽良心的鼓聲才有結伴遠行的可能。
哈維爾在《政治、道德與公民性》一文中說,“國家必須保持真正的人性”,“國家必須是有精神、有靈魂和有道德的”。但是,達到這個目的需要長期的努力,因為這並不能依靠“一套簡單的命令或指示”。“僅僅通過一種政體或者法律及指令是不能建成一個有道德、有精神的國家的,這只有通過包含教育和自我教育在內的長期複雜、永無終結的工作來進行”。這個估計也適合於我們今天以改良道德、砥礪品行、端正人心為目的的心智啟蒙。
心智啟蒙對人的可教育性和自我教育能力抱有審慎樂觀的態度,因為人雖然可以教育,也有自我教育的能力,但未必就有這樣的意願。而且,有的人出於自己的私利,或者因為把握著公共權力,還會千方百計地阻礙這種教育。心智啟蒙同樣也會避免對“知識必然導致行動”過於樂觀。它不懷疑知識是有用的,真理也是可知的(否則也就沒有心智啟蒙這回事了),但它並不認為人一旦掌握了知識或真理,就必然可以有所行動——“知而不行”不就是一個人心的弱點嗎?事實上,知識充其量只是行動的必要條件,而不是行動的充分條件,因為大多數的人在與自己利益不合,或者遭到外部脅迫時,即使自己覺得良心未泯,也不會有良心行為。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心智啟蒙自然必須做好“長期複雜、永無終結”的打算。
由於心智啟蒙必然是針對具體環境中特定問題的,它基本上只是對這些問題所形成或提供的一些小知識和看法,有待於進一步的擴展和補充。因此,不宜將過多的系統理論強加到這一以討論具體問題為主要目的的工作上。本書提出問題和探討問題的出發點是,啟蒙必須首先對個別事件或事例加以關注和思考,這種關注和思考是經驗性質的,不是從某種一般理論得出的推導。這是一種處理個別事件、事例,而非一般理論的方式,提供的只是個人的看法,不是普遍的真理。
本書第一部分討論的是個人良知和社會共善,以及這二者之間可能發生的矛盾和衝突,這種矛盾和衝突在民主的公共生活中是經常發生的,其不可避免讓我們看到,聽自己的良心鼓聲始終是必要的,但不可能獨自走得很遠。個人良知是社會道德的寶貴資源,不能保護個人良知的社會不可能是真正道德的。但是,民主社會的共善卻並不是孤獨個體良知的簡單相加。良心並不只是個人的,而且還是一種人與人互相聯繫的方式,因此,不能脫離一個人與他人的可能聯繫來瞭解他的良心。良心(conscience)一詞是從拉丁文conscientia一詞來的,原來的意思是人與人之間的“默契的知識”。與他人的聯繫其實早已包含在“良心”最早的意思裡了,良心不只是一種直覺的情感或情緒,而且更是一種基於道德知識的,針對具體事情和境遇的實踐性判斷,更重要的是,良心指的是一種由一些人分享的知識。
用單純自由主義的民主觀強調個人的“良心權利”,容易忘記或忽略良心其實一直是一種在人際分享的知識。法學家羅伯特·費捨爾(Robert K. Vischer)在《良心與共善》(Conscience and the Common Good)一書中指出,人的良心及是非、對錯觀念都受到來自外部的影響,一個人的良心是由於與他人有交往和互動,才變得清晰和明確起來的。正是由於一個人的良心具有社會性的一面,良心才對人的社會參與和行為具有指導的意義。良心所指導的不僅是他自己的個人行為,而且也是那些與他分享同一看法的其他人的行為。因此,良心把一個人與更大的存在群體聯繫到了一起,也使得良心對自己更有自信。在民主法治的制度中,政府沒有壓制公民良心的權力,個人良心在公民社會裡發揮作用,但並不比體現民主原則的集體良心更為優先。
本書第二部分討論的是人性自身的一些弱點、缺陷和幽暗意識,以及外力如何利用這些對人進行心理的和思想的操控。人在社會中表現出來的品格出錯和人心不正都與內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有關。每一種語言中都有大量關於人的品格出錯和人心不正的詞彙,如刁滑、奸詐、刁鑽、奸邪、詭詐,等等。這些詞彙通過同義詞的關係,形成了一個個“詞義簇”,辨認時會需要一些“指示詞”(如“欺騙”可以是刁滑、奸詐、刁鑽、奸邪、詭詐這個詞義簇的指示詞)。這些詞義簇的核心概念往往並不明確,在討論它們的時候,會遇到如何辨認和確定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找到一個普通人熟悉的指示詞。這就像做資料檢索時,需要知道“搜索詞”一樣。心理學和大眾心理學為許多這樣的不良品格、情緒、心理提供了案例分析及相關概念,可以在一個比較具體的知識層次上幫助心智啟蒙的工作。本書這一部分中所涉及的許多問題,如愚蠢、偽善、粗鄙、貪婪、輕信、偏執、忽悠、罪感、殘忍、非人化,等等,便得益於此。對人性問題的關注離不開心理學,也離不開哲學,心理學被稱為“隱藏的哲學”,心理學的良好基礎,對於瞭解人性的幽暗是不可缺少的。
人性的幽暗和軟弱限制了人的善行,也使得“惡”成為難以從現實生活中消除的危險。張灝在解釋“幽暗意識”時引用了美國神學家、思想家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1892—1971)的話:“人行正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可能,人行不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必需。”這是一個對人性卑劣和高尚雙重性的觀察。上帝給人良知,人於是能做好事。可是人性中還有陰暗和不完善的一面,需要有所制約。一方面,在設計具體制度時,需要將人性中的幽暗因素結合進去,如崔衛平所說,“在不同制度建設的背後,有著不同的人性觀作為鋪墊。恰當的人性觀,是制度建設之根基和保證。關於人性的幽暗意識,不僅是一門人性學說,還是一門制度建設之學說”。另一方面,人的內心需要有良心的力量和心智啟蒙的知識,否則難以察辨、抵禦我們自己的和別人的惡念惡行。如果沒有這樣的力量和知識,那麼,在制衡人性幽暗的制度不能建立,惡成為普遍規範的情況下,我們便會完全失去抵抗的能力,並失去抵抗的意願,除了自暴自棄、自甘墮落,再沒有別的選擇。
第三部分討論的是政治制度與民眾德行的問題,這既關乎古典哲學家關心的政體對公民的道德教化或道德敗壞,也關乎現代社會心理學所研究的“情境”對人的道德感知和社會行為的決定性影響。政體是一種統治形態,也是一種普遍的政治和社會文化生態。政體的制度本身可以成為現代社會心理學所關注的人的作惡情境,20世紀的極權統治便是這樣,這樣的環境是對人性的嚴酷考驗。人們普遍相信自己會聽從個人良心的指引,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展示的就是這樣一種作惡情境。他將此稱為“囚禁心靈的黑暗之地”。在那裡,“我們目睹了人性殘酷面的各色症狀,驚訝於善人如何輕易被環境改變,成為多麼殘酷的人,而且改變程度可以多麼劇烈”。情境的力量將權威、權力及被支配的個人行為之惡推向極致,“這股力量讓我們擱置自己的人性,並從身上奪走人類最珍視的品質:關心、仁慈、合作與愛”。
雖然現代社會心理學對人性的弱點和幽暗有了更深刻的體認,但並不對人性完全悲觀。用津巴多的話來說,瞭解情境的力量是為了“讓我們開始認識對抗心智控制的特定辦法”。因此,這樣的知識是為了幫助迫切需要的心智啟蒙,而不是鼓勵在作惡情境面前無所作為、自暴自棄。人性中終究有良善的力量,人是可以通過一些方法,利用個體的作為來挑戰環境與制度力量的。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馬克·吐溫說,“欺騙一個人要比讓他知道被人騙了來得容易”,同樣,開啟一個人的心智要比蒙蔽他的心智來得困難。有些個人善於抵抗,不屈服於誘惑,也許是天生就受到善良之神的嘉惠,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抵抗的能力是通過心智啟蒙獲得的,這種啟蒙是出於他們自己覺醒了的需要,也因為他們聽到了來自同路旅伴們的良心鼓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