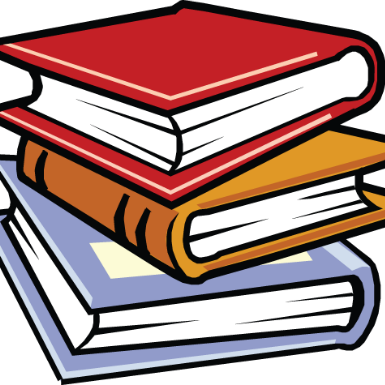在這段覺醒和改變的旅程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你要對自己富有同情心。記住,你是在試著改變一些自童年起就已經根深蒂固的思維和行為習慣,這很難。
把選擇的機會留給自己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幫助你開始改變,你可以繼續做個「聖母」,但這次全憑你自己的選擇。因此稱為有選擇的「聖母」。我從始至終沒有批評任何人的「聖母」行為。很多技能值得掌握,很多人求之若渴。我只是想幫助你擁有更多選擇的機會。那樣的話,當你實際做個「聖母」時,你的選擇只是出自你的自由意願。你不會再有被其他人的期望鎖在牢籠裡的感覺,換言之,「聖母詛咒」將被解除,並被轉化為一種賜福。
現在的我是什麼樣子?
如果你的這些行為已經保持了很多年,並且確實源自童年時期無意識中樹立的規則和觀念,那麼,要改變它們會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正如我們在第九章中看到的,別人會希望你「變回來!」你要承受這樣的壓力。不僅如此,如果「聖母」不再是你的默認設置,那麼,單單要弄清楚你真正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就夠難的了。
「聖母」型同事傑西卡告訴我,她費了很大勁兒去尋找所謂的「新角色」。她說:「我以前不是一個自信的人,所以,我不確定『她』是什麼樣子。我意識到,當我有自信後,我的說話方式變了,這個新的『我』有時候說起話來相當盛氣凌人。」另外一個咨詢者對我說:「對我而言,啟動『自動舵』模式並讓每個人都高興更容易一些。現在,我試著做真實的自己,我覺得自己赤裸裸地曝光在大庭廣眾之下,有點兒不知道該怎麼做。有點兒不自信和脆弱。」
傑西卡並不想變回過去的樣子,她覺得以前的她就是個「一直懷有歉意」的人,因此,她想出了一個大膽的解決方案,她決定向兩位信任的同事徵求意見。「我對他們說:『你能在我開始以盛氣凌人的語氣說話時提醒我一下嗎?我不喜歡用這樣的語氣說話。』結果是,這確實有幫助。有時候,當我看到他們臉上有意味的微笑時,我會打住,然後重新措辭。或者,突然住嘴,然後說:『我又那麼說話了,是不是?』反正這並不是世界末日。」
「健康的假我」
最早談及「真我」與「假我」的是心理治療師唐納德·伍茲·溫尼考特——《偽裝與真實》(Playing and Reality)一書的作者。他認為每個人都外帶這種「假我」保護層。他還提出,我們都需要一個「健康的假我」,讓我們能夠在大眾面前表現得禮貌而文雅。只有當我們與內心的「真我」失去聯繫時,我們才會有麻煩(或變得不健康)。
作為社會中的一員,我們不可能一直都只表現出真實的自己;我們要考慮別人的需求及每種情況下的社會要求。因此,我們倒是想要告訴老闆,他們的提議怎樣才能切中要點;或者,在乏味的聚會上脫掉所有的衣服,然後赤裸裸地在桌子上跳舞;又或者,當著婆婆的面發脾氣。然而,當我們想到這麼做的種種後果時,我們會選擇當前社會可以接受的行為方式(也可能不會)。
然而,對於很多人來說,好像還沒有一個已經準備好登上舞台中央的成熟「真我」。堅持一貫的「假我」也沒關係,但我們可以慢慢地試驗,找出哪些是「真我」的樣子,而哪些不是,直到我們對他/她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你可以把這個過程想像成試穿新衣的過程,而且你要試穿的是那些你只在家裡,或同樣安全及私密的環境下穿的衣服。
關於你想要歸入「真我」習性的一些特質,下面的一些看法會對你有幫助。某種程度上,它們就像高空走鋼絲的人下面的安全網,讓你有勇氣去改變。
富有同情心,但要有限度
心理學教授蕾切爾·特賴布是第一個讓我知道這一點的人。她是我在東倫敦大學讀高級輔導心理學碩士時的課程主任。她看起來是真心關心學生們不可避免的各種困難、壓力及不安。她是一名善於站在對方的角度想問題的聆聽者,並且會努力提出一個創造性的解決方案,甚至會為了解決學生的問題而委屈自己。
有一天發生的事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離交作業的最後期限只差一周的時候,可以預見的是,班上相當一部分同學都在擔心無法按時交出論文。那天上午上課時,到了最後的提問時間,有幾位同學開始試著用甜言蜜語哄得老師延長最後期限。他們給出了各種理由:生病、搬家、父母身體不適、事情多,等等。特賴布仔細地聽他們的各種理由,同時點頭表示同情,然後,她給出的答案卻是「不行」,語氣很客氣,但很堅定。她說,任何人如果確實需要延期,可以填寫相關申請表,並將申請表與相關證明(如醫生的診斷報告)一起交到辦公室。否則,最後期限不能變。
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客氣的拒絕」。這也是一種很不受歡迎的拒絕,一些學生表示很生氣。但她很堅持,她的面部表情依然帶著真誠的同情。我對此印象很深刻,以至於久久不能忘記。這件事讓我想到了新的可能性,一種新的為人處世的方式。有限度地表示同情包含了一種思維方式,即「我有權設定限度」,或者「即使人們不喜歡我的決定,我仍然是一個值得尊敬並令人喜愛的人」。
很多「聖母」都覺得設定限度很難,並且幾乎沒有什麼實踐經驗。它總是被人們掛在嘴上,但如果沒有實際體驗,你很難明白其中的意義。有些咨詢者發現,設定限度可以讓他們覺得,自己與其他人之間存在某種起到隔離作用的東西,讓他們不再覺得別人的情緒正在滲入自己體內,也就不再會輕易對別人的情緒產生過度的同情,或是在自己明明想拒絕的時候仍然答應別人的請求。通常,這就好像他們周圍多了一個光保護圈(選擇你自己喜歡的顏色),或是像有機玻璃泡那樣有形但透明的東西。有位咨詢者想像著她的夢想小屋周圍有一道牆,牆上有數扇鐵門,還有對講機。然後,當她那好支使人的前男友或喜歡打擾人的母親來叫門時,她可以自己決定是讓他們進來,還是把他們擋在門外。這最終將轉化成為自尊感和安全感。
小小成功,而不是部分失敗
在這段覺醒和改變的旅程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你要對自己富有同情心。記住,你是在試著改變一些自童年起就已經根深蒂固的思維和行為習慣,這很難。最起碼跟讓你改掉咬指甲、玩兒頭髮或安慰性進食這類習慣一樣難。
把任務細分,一小步接一小步地進行。確保你能夠注意到自己的每一次進步,並對自己進行獎勵,不管這一進步對那些不屑一顧的批判者來說多麼微不足道。下面是傑西卡所說的話:
治療最有幫助的地方是讓我認識到,所有挑戰加在一起是一項十分複雜的任務。就連「不要對自己不喜歡的人笑」,我都覺得是個巨大的挑戰,但我還是想要面對這個挑戰並獲得成功。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我很想有一天能夠帶著百分百的自信去處理工作中的各種情況,並很快得到人們的認可。你讓我知道,我需要小步前進,並把這些小步當作小小的成功,而不是部分的失敗。因此,即便我只能對著某人說「是的,但是……」,而無法給出一個響亮的拒絕,這也是在向著好的方向前進,我可以對自己好一點兒,我覺得自己做得還不錯,下次還可以更進一步。
佩妮的約會
佩妮,那位因為不想讓愛她的男友失望而結了三次婚的女校長,給我發來一封郵件,向我講述她是怎樣進行行為實驗的。你也許還記得,她那天晚上與一位男士有約,她對那位男士並沒有太強烈的感覺,所以想要試著表現得不那麼熱情,而只是有限度地顧及他的感受。「我發現這確實很難,」她信中這樣說,「他在一家非常時尚並奢華的餐廳訂了位子,這讓我立刻產生了壓力和愧疚感,讓我覺得必須對他好,不能讓他失望。」
儘管如此,佩妮還是在約會之前先準備好了她的「工具」(見第七章)。她非常清楚,在面對問題學生及員工時,她是能夠「和善地保持堅定」的,她也知道,當她對「死板的個人規則」產生質疑時,她可以使用相關技能。這個「死板的個人規則」是:「一個女人永遠不該讓愛她的男人失望。」於是,在吃完昂貴而奢侈的一餐飯後,她看著他的眼睛,表現得誠實而友善。她對他說:「你真的是一個很可愛的人,但是我現在的生活中要面對很多事,如果我說希望我們的關係再進一步,我其實是在欺騙你。」
佩妮寫道:「誠實地說,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意識並有目的地拒絕別人。那是個轉折點。他很沮喪,但如果我任其發展,事情反而會更糟糕。」
那些「聖母」的後續故事
現在,我們來說一說本書中提到的其他人的後續故事。希望他們的實際體驗會給你鼓勵和希望。
哈米什怎麼樣了?
哈米什很努力,試著接受並整合他自身的所有側面,包括那些被他貼上了「拙劣陰暗面」標籤的側面。在我們的治療結束時,哈米什仍不喜歡這些側面,但他知道,它們是他完整而真實的一部分。他也知道,只有把這些側面展示給別人,他才能與他們建立起親密而長久的關係。在建立並維持友誼方面,他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主要歸功於他不再限制自己只做個「受歡迎」的「聖母」,而願意將他的側面展示給別人。
哈米什換了一份新工作,工作地點在另外的城市,所以他終止了治療。他覺得,在新工作中,他可以徹底改造自己,以他想要的方式重新開始(他採納了「聖誕節前千萬不要微笑」這條建議),定量展示他的燦爛笑容及迷人的笑話,克制他過度樂於助人的傾向。
在那之前,他已經開始感知內心壓抑的憤怒,並識別腎上腺素漩渦般翻湧時的狀態。他知道,這意味著他曾經一直在刪除一些不和諧的想法(如對粥鍋的憤怒),而他曾試著將它們表達出來,尤其是對他的妻子表達出來。但這樣的變化導致他們之間產生了矛盾。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解決了這些矛盾並繼續並肩前進,還是他們的關係無法承受這種新的動力。如果我假裝一切都有個美滿的結局,那我是在誤導你,但我希望事情能如他所願。
這裡提醒一句:有時候,在一段關係中,如果你屬於被動一方,即便你較為自信,你也不會有安全感。有時候,「變回來!」的壓力會更為強烈。如果是這種情況,怎麼覺得安全就怎麼做:求助、找警察或去個安全的地方。夫妻心理輔導可能會有幫助,但也只限於你們事先已達成共同的安全協定的情況下。
阿曼達——「聖母」型伴侶
我們一起創造了「憤恨計」這種東西,用於幫助阿曼達監測她在與西蒙的這段關係中的「過度付出」問題。這之後,他們的生活開始發生了變化。起初,她和西蒙的關係進入了一個艱難期,西蒙似乎變得疏遠,阿曼達也很恐慌。但是,我鼓勵她重新找回那些草率丟掉的友誼和興趣,而這段關係似乎也隨之變得更加平衡。
《憤怒之舞》一書的作者哈麗特·勒納曾經說過,在一段親密關係中,久而久之,一方會習慣性成為「過度責任承擔方」,而另一方則會成為「較少責任承擔方」。早期的阿曼達像瘋了一樣過度承擔責任,而這已經對她產生了不良影響。後來,她把更多的時間分配給了自己,並真正享受自己的時光。這幫助她重新為自己的「電池」充滿了「電」。她不再為了一個電話等到深更半夜。後來,她強迫自己把自己的健康問題、工作中遇到的危機以及自己的感受都告訴西蒙。她承認,那樣真誠地說出自己的感覺和弱點是最困難的事,但那麼做讓他們變得更親密了。「我們的關係變得更真實了,我想,與此同時,我也更有勇氣做自己了。」
英迪拉和BEAR四步法
在我們的療程結束後一年之後,英迪拉反饋了這樣的信息:
我使用了你教我的BEAR四步法。把它應用到我的家人身上很難,因為他們不太接受我的改變(或者,我自己也一樣?)。儘管如此,它還是幫助了我,讓我不再以一種非黑即白的方式去看待事情。它提醒我,我不僅要接受別人的想法,還要接受我自己的想法,這對我來說確實很難。當我在腦海裡反覆想著BEAR四步法時,我不僅能讚揚別人,同時還能讚揚我自己。
因此,在面對我母親時,當她發郵件來指責剛和姐姐吵過架的我有哪些過錯時,我使用了BEAR四步法。我沒有覺得自己可憐,也沒有責怪自己或回一封充滿暗諷的郵件給她。我只是花了一點時間想清楚這件事,然後向一個朋友發了一頓牢騷。在那之後,我開始相信,她可能也很痛苦,因為兩個女兒彼此不說話,還都向她抱怨,那感覺一定糟糕透了。我在給她回的郵件裡表示理解她的痛苦,告訴她我需要她怎麼做,以及她如何能幫到我,並沒有詳細爭辯我和姐姐究竟誰對誰錯。結果是,她不再理會這件事,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這讓我對自己和自己所擁有的權利有了新的看法,讓我可以在不責備自己或其他人的情況下堅持某個想法或做出相應的情緒反應!
現在,在與家人交流時,我覺得自己更自信了,即便是自己心煩的時候,我也能更好地處理與他們之間的問題了。
麗貝卡的故事
我把這個故事放在這裡是因為,它向我們展示了,主人公是如何運用本書中介紹的一系列理念和策略來處理她的高恐懼等級問題的。
我們在前面簡單地提到過麗貝卡。她的故事很有啟發性。麗貝卡是一位靚麗的年輕女性,從事媒體工作。她大膽地嘗試了三個方面的改變:思維、感覺及行為。她在這個過程中也確實得到了回報。她的生活中仍有很多問題要處理,但她已經開始著手以更好的方式去解決它們。
當她得到自己夢想已久的工作後(擊敗了數百個競爭對手),她很高興,因為她的上司很欣賞她,很熱情地幫助她,以便她能盡快進入狀態,也教了她很多秘訣,鼓勵她大膽地追求成功。「我想,當他開始說我有多特別,並在私底下對我更加關注時,例如帶我去吃午飯,我本應該注意到這些警報信號。」麗貝卡對我說。然而,她當時只覺得受寵若驚,並且充滿感激(這也可以理解)。當她可以勝任另一職位並離開他的管轄範圍後,她很興奮,並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但是,令人吃驚的是,他仍然想要保持他們之間「特別」的關係,並不停地發來郵件,提議一些不適當的工作以外的見面,比如喝東西或吃飯等。這讓麗貝卡越來越感到不安和有壓力,基本上讓她的生活陷入了痛苦之中。「我不知是什麼原因讓他對我產生了興趣,某種程度上,是我的錯,我不應該惡意地對他。」在治療期間,麗貝卡做了很多努力來建立她的自我價值感。她每天都對自己說「我愛你」,寫「一日三好」日記,還進行了「每天讓人失望」的練習。但是,她太害怕讓自己之前的上司失望。我們討論了「客氣的拒絕」的情況,並做了相關的角色扮演,腳本是她實際上可以用到的。在經過一場「不加判斷的創造性頭腦風暴」後,她面前有了一堆的選擇,而她最終選擇了最簡單且最安全的方法作為開始:將她的辦公桌移到他視線以外(因為他時常盯著她看)。
後來,有一次我們見面時,她看起來很高興,整個人充滿了自信,無拘無束,再也不是一副焦慮的樣子。「我與他見了面!」她說:「他發了很多郵件請求我見他一面,我最終答應了,但只在我做好極其利己的心理建設(她很喜歡雪柔·理查森書中的這部分內容)並感覺自己足夠強大之後才答應與他見面。」
「噢,」我問:「發生了什麼?」「好吧,我用的大多數方法都是我們討論過的。我使用了『客氣的拒絕』,並感謝他來見我,但我非常冷靜而清晰地告訴他,對於一名高級男性主管和一名初級女職員而言,這樣的關係並不適當,不應該再繼續。他仍然對我說,他覺得我很特別,他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而我使用了『卡殼唱片技巧』重複著相同的話。十分鐘後,我結束了這段談話,然後離開了。」我問道:「那現在怎麼樣了?」「我覺得很神奇!我現在真的很快樂,無拘無束,覺得自己有權利這樣做。他有什麼樣的感受是他的事,而我知道自己做得對。」
「故態復萌」與「緊急求救卡」
生活是不可預知的,所謂掌控其實只是一種幻覺(想想自然災害就知道了),艱難和不幸時有發生,而且通常都發生在我們毫無準備的時候。正是在這些時候,我們往往會退回到陳舊且無用的思維、感覺及行為模式中。在心理治療過程中,這被稱為「故態復萌」,但我們可以一起來制定一個計劃,幫助你應對這種情況。
我設計了一個便於使用的「緊急求救卡」的模板。這個模板是圍繞戰時使用的摩斯密碼危難信號SOS設計的,這個信號的意思是「救救我們」。我想,這個詞用在這裡非常恰當,因為,就我自己和無數咨詢者的經驗來看,當「故態復萌」時,事情會變得極其暗淡和令人絕望。
「緊急求救卡」模板:
1.說出來(SPEAK):想打電話聯繫的自己信任的人是……
2.「走開(閉嘴)!」等(……OFF):對於批判性聲音的最佳回應方式是……
3.安慰自己並變得強大(SOOTHE AND STRENGTHEN):最喜歡的安慰自己及分散注意力的活動是……
拿一張可隨身攜帶的卡片或紙,在空白處寫下你自己的想法。其中,有些你可能已經很清楚,有些則需要再好好想想。首先,在「S」後面列出一兩個支持你並且深得你信任的人(這裡不要考慮應不應該的問題,只列出你覺得可以與之分享你的弱點且不會評判你,或給出太多建議的人)。接著,在「O」後面,寫下你在覺得自己足夠強大及自信時能夠對批評性聲音做出的最佳反應。最後,在「S」後面,寫下能夠幫助你安慰自己並讓自己變得強大的活動,這有時也被稱為「健康的分心」,因此,試著不要列出讓你覺得愧疚的不健康的東西。
一旦冷靜下來後,你便可以考慮下一步驟,即創造性地解決問題。不過,在開始使用大腦中解決問題的功能區之前,你要先找到十足的安全感。
莫妮卡的「求救卡」
我們在第五章中提及莫妮卡,她從小到大都在努力避免父母的批評。她的母親堅定地認為「批評能激勵孩子」,並且,即便她女兒後來勇敢地拿出證據表明事實剛好相反,她也毫不動搖。
當地一家電台一直在邀請莫妮卡上他們的節目,希望她能夠談一談她參與過的一個社區項目。她告訴了父母她接受採訪的時間。(這可能並不是明智之舉)在回想起這件事時,她苦笑著告訴我,這件事應該是拉響了她的「救贖性轉折點」警報,因為她後來才意識到,她當時很可能是下意識地希望能借此得到父母的讚揚和肯定。
那天晚上廣播節目結束後(一切進行得很順利),她的父親打來電話,告訴她家裡的某項安排。電話快結束時,他隨口說道:「我覺得那個女人主導了整個訪談,你應該多為自己爭取說話的時間。」事情就是這樣。沒別的,再沒有其他評論。莫妮卡說,她當時覺得自己好像快要完全喘不上氣來了。她盡快掛斷了電話,一口氣喝下一大杯酒,然後掉下了眼淚。沒有一絲力氣的她倒在沙發上,只覺得沮喪,失去了所有動力。
幸運的是,她記起了她的「求救卡」。她把它從錢包了拿出來,開始按照步驟使用它。她發了條短信給她最信任的朋友,並約好找時間好好聊聊。只是這一步,她已經冷靜了下來。她反省了自己的情緒,然後意識到,另一道希望之光覆滅了。她內心的小孩兒覺得自己被拒絕和擊垮了,正如她不再對任何事情抱有希望。「重點是什麼?」批判性聲音響起了,「你做任何事都做不好。」這時,她看著自己「求救卡」的第二條:對於批判性聲音的最佳回應方式是:「走開,你們這些貪婪鬼。我是成功的,因為我在嘗試。」
此外,「求救卡」還讓她想起,她可以做一些安慰自己並提高自己情緒的事情,這樣會更好。於是,她泡了個香噴噴的熱水澡,又放了自己最喜歡的音樂。然後,她穿上了最柔軟的睡衣,準備早點睡覺。就在這時,她突然有了一個似乎頗具突破性的想法:她決定,如果第二天家裡任何一個人以一種批判性的口吻提及她的採訪,她會用準備好的方式回應。她會說:「你看,我只是和你們一樣的普通人,在接受電台採訪時當然會覺得沒底氣和緊張。你這樣批評我傷害了我,其他人也一樣。」莫妮卡並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有機會說出這些話,或者,即便她有機會,她是否能夠說出這些話。但是,有個「腳本」能讓事情變得更清楚,也能夠讓她更為冷靜。她覺得自己更成熟了,並被賦予了某種權力。
她參加了第二天中午的家庭聚餐,但沒有人提及那個電台節目。她有些如釋重負,但同時又有些失望。但由於前天晚上使用了「求救卡」,他們提不提似乎也沒那麼重要了。她認識到,父親的批評可能只是出於他的恐懼和不安,她對他還是有一些同情的。
很多咨詢者都使用過「求救卡」。他們把卡打印出來,並把它們放在顯而易見但又比較私人的地方。薩曼莎打印了不同尺寸的「求救卡」,把它們疊起來,一張貼在臥室的鏡子上,一張貼在冰箱上,一張放在錢包裡;艾拉把她的「求救卡」存在了電腦及手機文檔中;蘇西則給她兩個最要好的朋友每人發了一份她的「求救卡」,讓她們感覺事情不妙時用一種特殊的代碼文字發短信給她,因為她知道,她的默認處理機制會倒退回來,並把她孤立起來(就像她小時候會在遇到衝突時躲進自己房間一樣)。
越少,越好:我從手臂受傷事件中得到的禮物
我用我自己的例子開始了這個課題,因此,很多來參加講習班的人經常問我:「手臂受傷之後發生了什麼?你現在痊癒了嗎?你是否已經打破了詛咒?」好吧,我的傷已經好了,但詛咒還沒有打破。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這是一項尚在進行中的工作。
在面對大多數人時,我不再過度付出。但對我來說,面對那些陪伴我最久的人,才是最具挑戰性的事。我還會倒退,在不知不覺中退回到以前「陽光小美女」的樣子。但是,我還是有進步的。正如本章標題所表明的那樣,我可以自己決定什麼時候表現出親切,什麼時候幫助別人,什麼時候富有同情心,什麼時候表現得有趣、活潑,或做出我想要展示的「可愛」行為。但是,我也可以選擇其他行為,而不會覺得自己是一個不討人喜歡或遭到排斥的壞人。當然會有人不喜歡我、排斥我,而現在,我覺得這是可以承受的,也是現實的,這是我照顧自己並滿足自己所需應該付出的一點點代價。
手臂受傷事件之後,我還遇到了其他健康方面的挑戰。這些挑戰迫使我更近距離地去聆聽身體的聲音,並在合理的範圍內滿足它的需求。當我感到疲倦時,我會允許自己放下一些事情,然後好好休息一下。於是,我現在躺床上休息的時間更長了!
到目前為止,你可能已經發現,我喜歡自創一些說法,比如「越短,越好」,它們能夠幫助我(及咨詢者們)記住我們自己想要怎樣的生活,並指導我們做出選擇。在手臂受傷這個令人頓悟的事件發生後,我最奉行的一句話便是「越少,越好」。我將這句話運用到了我人生中的所有整理工作中,從丟掉那些沒用的、不適合我的或我並不喜歡的東西,直到像莉茲那樣減少我的社交活動。現在,我在試著只和下面這些人交往:我真正覺得交情深的人、能夠讓我放心展露自己的弱點和真實的我的人,以及我能夠求助的人。
這與「500臉書好友」綜合征的情況恰恰相反。有人有這麼多的好友,這讓很多只有少數幾個親密及信賴的朋友的人感到很不好意思。當今社會,擁有大量網友也變成了眾多「應該」中的一種,我們如果不遵從這種「應該」,似乎就會覺得自己很失敗。
臨終前的遺憾
上個月,我在一位朋友50歲的生日宴會上聊起了「聖母詛咒」。「哦,你應該讀一讀這本書,是一位從事臨終療護工作的護士寫的,」這位朋友說,「關於人們去世前最遺憾的事,有些聽起來跟你書中所講的內容很像。」我隨後便買了這本書,名為《臨終前最遺憾的五件事》(The Top Five Regrets of the Dying),作者是布朗妮·韋爾。果然,根據她的經歷,排在第一位的遺憾是:我希望我能夠有勇氣在生活中做真正的自己,而不是為別人對我的期望而活。排在第三位的是:我希望我能夠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感受,而不用為了與別人和平相處而壓抑它們。(為了滿足你的好奇,我還可以告訴你排在第二位的是:我希望我可以在工作上少花些時間,把更多的時間留給我愛的人們。)
這些臨終遺言能幫助我們找到不同於以往並可能比以往更好的生活方式。如果我們的人生目標中有一項是「不要遺憾」,那麼,聽一聽這些最常見的遺憾是有幫助的。這些遺憾通常不是「我希望我去了臨時秘書的送行聚會」,或者甚至是「我希望我能夠環遊世界,在科羅拉多大峽谷蹦極」;它們似乎可以歸結為,有勇氣做真正的自己,並讓人們(尤其是我們愛的人)知道我們真實(合理)的想法。
重新繪圖
還記得我們在第二章中介紹的練習嗎?請你在從「聖母」的頭部延伸出來的線型圖中寫下你想要向世人展示的品質。然後,在下面的三角形長袍中寫下你試圖隱藏的東西。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將你破除「可愛的詛咒」的旅程壓縮成一張新圖。下面講你可以怎麼做。你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成這段旅程,就像西天取經一樣,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並且一路上必將充滿障礙、未知的洞坑、轉向及彎路。但是,慢慢地,你將不再覺得自己受到了詛咒,而是發現自己其實被賜予了做個「聖母」的技能和品質,而被「聖母」對待的人不只包括其他人,更包括你自己。
右面是我重繪的圖:

在輻射向外的線型圖中,我填寫的是:坦率、誠實、有趣、精力旺盛、認真、富有同情心、界限分明(但我會有選擇地去表現,不會強迫自己必須去以某種方式行事);而在長袍內(不再讓它們大肆翻湧,而是妥善處置),我寫下:脆弱和恐懼,對於它們,我只會謹慎地與我覺得放心的人分享。
也許,在理想的世界中,沒有什麼是讓人覺得丟臉或者需要隱藏或壓抑的,我們都是絕對完美和真實的人。但是,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中,新圖展現的才是我們切實想要成為的樣子:穩妥起見,需要真實的自己與溫尼考特所謂的「健康假我」的綜合體。當我完成某種改變時,比如拒絕某個難以應付的人,我會表揚自己,也許還會請自己吃點兒好吃的東西作為獎勵。
你也一樣可以做些改變,我知道你可以。對於勇敢嘗試新事物及打破舊有模式,人類有著驚人的能力,我對此非常有信心。一旦你開始這段旅程,每一步成功都會賦予你權力,並鼓勵你走向新的成功。你會發現,你可以每次只邁出一步,在保證安全的同時,也要照顧好自己的感受。這能讓你看清楚你所有的美好品質、怪癖及優勢。最終,你將打破「聖母詛咒」,做回你本來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