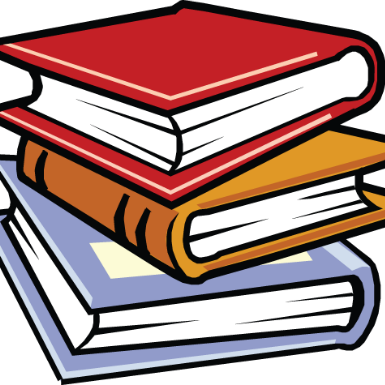在本書的開頭,我提出,感受對理性有很強的影響,兩者需要的大腦系統是相互聯繫的,而上述系統又與調節軀體的系統交織在一起。
我提出的事實大體上支持了這些假設,希望吸引研究者進一步的研究,得出新的研究結果,對之進行修正。感受似乎依賴於由多個部分組成的系統,這個系統與生物調節緊密結合。推理似乎也依賴於特定的一些腦區,這些腦區中的一部分恰好也加工感受。因此,在解剖和功能層面,可能存在從推理到感受再到軀體的連接軌跡。我們好像被一種推理的激情所支配,這種驅力源於大腦的深層核心,並滲透到神經系統的其他層面,以感覺或無意識偏差的形式出現,並指導著決策。推理,從實際層面到理論層面,都是構建在這種先天驅力的基礎上的,其過程類似於掌握一門技術或技藝。沒有這種驅力,你就無法掌握推理。但是只有驅力,你也不一定能夠自動掌握推理。
如果這些假設得到支持,那麼推理就不是純粹的理性過程了。這一觀念是否有其社會文化意義呢?我相信確有意義,而且這些意義大都是積極的。
瞭解感受在理性過程中的相關性並不意味著推理不如感受那麼重要,或推理只是備胎,或我們就不應培養推理能力。相反,理解感受的普遍作用可能會使我們增大感受的積極效果,減少可能的傷害。具體來說,在不降低正常感受引導推理的作用的情況下,人們會希望在規劃和決策過程中避免異常感受帶來的影響或被感受所操縱,從而作出錯誤的決定。
我不相信有關感受的知識會降低我們實證研究的傾向。有關情緒和感受的生理學的更多知識能使我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科學觀察的缺陷。我的論述不應該削弱我們控制外部環境以服務個人和社會利益的決心,也不應該削弱我們發明或完善那些使世界更美好的文化工具,即倫理、法律、藝術、科學和技術的決心。換句話說,我並沒有要求大家一定要接受我的觀點。我必須強調這一點,因為提到感受,經常引起這樣的印象,即過分關注自我、無視環境、任性妄為。實際上,我的觀點恰恰相反。有些人可能並不擔心上述問題,但會擔心,對感受的過度重視會削弱我們堅持浮士德條約的決心,而這種條約帶來了人性的進步,分子生物學家岡瑟·斯滕特(Gunther Stent)就是代表(1)。
令我擔心的一點是,我們一方面接受了感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卻不去努力瞭解其背後複雜的生物和社會文化機制。這種態度的最佳例證就是,通過膚淺的社會原因或神經遞質的作用來解釋感受損傷或非理性行為,這種解釋思路現在充斥在各種平面媒體和視覺媒體中。還有人試圖用醫療藥物和非醫療藥物來糾正個人和社會問題。這種對感受和推理本質的理解不足是「抱怨文化」的特點之一(2),它引起了我們的警覺。
本書所概述的對於人類機體的觀點,以及從各種研究結果中推論出的感受與理性之間的關係都確實表明,理性的增強可能需要我們更多地考慮到內部世界的脆弱性。
在實踐層面上,理解感受在推理中的作用有助於幫助我們理解當前面臨的社會、教育和暴力問題。在這裡討論這個問題不太適合,但我要提一句,強調當前感受和未來預測結果之間的明確關係,可能會對教育系統有所幫助;如果兒童過度暴露在現實生活、新聞廣播或視聽小說的暴力內容中,他們在習得和實施適應性社會行為時,情緒和感受的強烈程度就會降低。大量間接接觸暴力卻沒有道德框架的約束,會使兒童對暴力愈發不敏感。
笛卡爾的錯誤
如果不提及笛卡爾這位在西方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中極具影響的科學家,不提及他在身、心、腦三方面的觀點,我就無法向大家呈現本部分內容。正如你所看到的,我關注的是笛卡爾身心分離的二元論觀點以及這個觀點的幾個現代變體。例如,一種觀點認為心智與大腦有關,但僅限於將心智看作軟件程序,運行在一個稱為大腦的計算機硬件上;或者大腦和軀體是相關的,但只是說前者必須在後者的生命支持下才能生存。
那麼笛卡爾的錯誤到底是什麼呢?還是用更好的說法,不禮貌、不友好地問一句,笛卡爾到底哪一點錯了呢?有人可能會先抱怨並責備他讓生物學家直到現在還在使用機械論作為生命過程的解釋模式。但這也許不是很公平,所以可能會繼續轉向那句「我思故我在」。這也許是哲學史上最有名的一句話,其首次出現於1637年法文版的《方法論》(Discourse on the Method)的第四部分,還有1644年拉丁文版的《哲學原理》(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的第一部分中(3)。從字面上來說,這一說法和我認為的心智的起源以及心智與軀體關係的觀點正好相反。這句話表明,思維和思維意識是「存在」的基礎。既然我們都知道笛卡爾認為思想是一種與軀體完全分離的活動,那麼這句話的確對將「思考的東西」(res cogitans)從具有外展性和機械性的軀體部分(res extensa)中分離出來進行了頌揚。
在人類出現很久之前,生命就已經存在了。在演化的某個時刻,一個基本的意識出現了。有了這個基本的意識,就產生了一個簡單的心智。如果心智的複雜性越來越高,思考出現的可能性也就越來越大,進而用語言來溝通和組織思維也成為可能。對那時的我們來說,「存在」是先於「思考」而出現的。現在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也是先存在,然後再思考,我們存在之後我們才能思考,我們思考只因我們存在,因為思考的確是由生物的結構和運作所引發的。
當我們把笛卡爾的聲明放回它所屬的時代,我們可能會想一會兒,這句話的含義是否與現在所代表的含義不同。可以看一看,這句話是否只是對感受和推理的一種肯定,並沒有涉及其起源、成分和時間特徵呢?這句話是否只是笛卡爾為了調和宗教壓力而創造的呢?後者只是一種可能性,但無從證實這一可能。笛卡爾把他常引用的一句話作為他的墓誌銘,「Bene qui latuit, bene vixit」,其意義是「隱藏得很好的人,才能活得好」,這句話來自奧維德(Ovid)的《哀怨集》(Tristia,3.4.25),難道笛卡爾隱秘地放棄了自己的觀點嗎?對於前者,我認為笛卡爾寫的就是他自己想表達的。他寫下那句話的時候,他認為這個觀點確定無疑,且任何質疑都無法動搖它:
……評論說「我思故我在」這個真理確定無疑,即便是最刁鑽的懷疑論者也無法動搖它,我決定,將其作為我追求的哲學的首要原則。
這裡,笛卡爾在為自己的哲學打下邏輯基礎,這個說法和奧古斯丁(Augustine)的「我錯誤所以我存在」(Fallor ergo sum)相類似(5)。在下面幾段中,笛卡爾明確地澄清了自己的觀點:
據此,我知道「我」是一種物質,其全部本質或性質就是思考,而它的存在並不需要空間,也不依賴於任何實在物質;所以這個「我」就是我所說的靈魂,獨立於個體,比後者更容易理解;即使沒有軀體,靈魂也不會消亡(6)。
這就是笛卡爾的錯誤:在軀體和心靈之間劃分了一道鴻溝,即在有形有象、機械動作且無限可分的軀體,以及無形無象、無法觸及且不可分割的心智間,劃分了一道鴻溝;他認為,推理、道德判斷以及肉體疼痛或情緒動盪所帶來的痛苦存在於軀體之外。具體來說:他將最精巧的心智過程,與生物有機體的結構和運作分開了。
現在有些人可能會問,為什麼要抓著笛卡爾不放,為什麼不選擇柏拉圖?柏拉圖對軀體和心智的看法更為激進,《斐多篇》(Phaedo)就可以體現這一說法。為什麼要喋喋不休地抓住笛卡爾這個錯誤?畢竟,他的其他錯誤比這個錯誤更嚴重。如他認為熱量使血液循環,還有血液中的細小顆粒蒸發成「動物精神」,從而使肌肉運動。為什麼不攻擊這兩個錯誤?原因很簡單:我們長期以來就認識到他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是錯誤的,並且血液循環的方式和原因已經得到了滿意的解答。但是考慮到心智、大腦和軀體的問題時,情況就並非如此了,笛卡爾的錯誤還是極具影響力。對許多人來說,笛卡爾的觀點被認為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重新審視。
在20世紀中期,笛卡爾的心智無實體的觀念使人們將心智比喻成軟件程序。事實上,如果心智是與軀體分離的,或許人們可以不借助神經生物學而去理解它,也不需要神經解剖學和神經化學的知識。有趣但矛盾的是,許多認知科學家認為自己不借助神經生物學就可以探索心智,但他們不承認自己是二元論者。
可能在有些神經科學家的觀念中還殘存著笛卡爾二元論的思想,他們堅持認為,只關注大腦就可以完全解釋思維,而不用考慮有機體的其餘部分和周圍的物理環境和社會環境,實際上,他們也忽略了以下事實,即環境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有機體之前行為的產物。我抵制這種觀點,並不是因為心智與大腦活動沒有直接的關係,顯然並非如此;而是因為這個說法是不完備的,讓人無法認同。心智來源於大腦是無可爭辯的,但我更希望評估這個觀點,並考慮大腦中的神經元如何實現思維性的運作。就我而言,後者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笛卡爾的二元論思想似乎也塑造了西方醫學對疾病的研究和治療方式(見後記)。笛卡爾的學說同時滲透到了研究和治療領域。因此,軀體疾病所造成的心理後果通常被忽視或沒有被認真考慮。以外,更被忽視的是心理衝突所產生的軀體後果。笛卡爾確實改變了醫學的發展歷程,顛覆了心智存在於軀體的觀點,即便後者從希波克拉底時代到文藝復興時代都占主流。如果亞里士多德瞭解這一切,他該對笛卡爾有多不滿啊!
笛卡爾錯誤的各種版本,使人們忽視了以下事實,即人類心智根植在複雜且脆弱、有限但獨特的生物體中,他們掩蓋了在這種脆弱的、有限的和唯一的知識中隱含的悲劇。人們無法意識到固有的悲劇,所以很少想到減少這些悲劇,因此也對生命的價值不夠尊重。
關於感受和推理的說明,以及我討論過的大腦與軀體之間的相互聯繫,都支持我這本書中的最一般的觀點:有機體的角度對從整體上理解人類心智是必需的;心智不僅必須從非物質領域轉移到生物組織的領域,而且還需要與一個完整的、整合了軀體和大腦的有機體相聯繫,此外還需要與物理環境和社會環境充分互動。
然而,我所設想的具身心智,並不放棄那些構成靈魂和精神的最精妙的層次上的運轉。從我的角度來看,正是靈魂和精神,加上尊嚴和人性,才能形成有機體展現出的複雜性和獨特性。也許作為人類,我們可以做的最不可或缺的事情,就是每一天提醒我們自己和其他人,人類具有複雜性、脆弱性、有限性和獨特性。這當然是困難的工作,難道不是嗎?將精神從不存在的基座移到其他某個地方,同時保持其尊嚴和重要性;承認其謙卑的起源和脆弱性,但仍接受其指導。但是,如果我們不加以堅持,那還不如讓笛卡爾的錯誤就這樣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