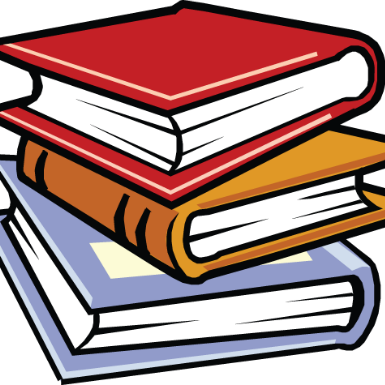詩人尹麗川說:「一下雪,北京就變成了北平。」北京和北平,一字之差,這裡頭的寧靜與詩意,只有「我們」才瞭解。大山們就算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兒背得滾瓜爛熟,恐怕也難以真正體會。
哪怕老捨筆下「處處有空兒」的北平已經變成「天天給人添堵」的北京,對於這座城市,我們依舊一往情深。比方說,都是Fifth Avenue(第五大道),我相信走在曼哈頓的第五大街和中關村的五道口,你的心情一定會有很大不同。那些沿街叫賣的紅薯攤,坑坑窪窪的行人道,像布朗運動無規則四下逃竄的路人,還有各種撲面而來的市井氣息,所有這一切,都讓你備感親切和溫暖。
你當然也會抱怨北京,就像Sex and the City(《慾望都市》)裡的Carry 一樣咒罵曼哈頓,但是罵歸罵,罵完之後,矯情的白領麗人照樣還會站在第五大街上張開雙臂大聲喊:「我愛你,紐約!」還不允許別人說紐約的不好。
同樣矯情的還有下面這句話,說母校是什麼,母校就是那個自己怎麼罵都可以,別人卻不能說一句不好的地方!自己可以罵,是因為母校的確坑過你,別人不能罵,是因為別人一罵你就感覺在罵你自己。
罵母校就等於在罵自己——儘管這句話一臉欲拒還迎的獻媚和撒嬌,但我還是必須承認它的確有些道理。如果做道填空題,刪去「母校」兩個字,填上「兒子」或「祖國」,道理似乎仍舊說得通,原因很簡單,這些字眼前面都可以加上定語「我的」,並且,還不是所有權意義上的「我的」,而是自我認同意義上的「我的」。
自我認同的奇妙之處在於,它不但把「我的」升級成「我自己」,而且還可以在價值論上進一步把「我的」變異成「好的」。社會心理學家說,一個心智健康的人自我評價往往會高於他人評價,將自我想像成是好的心理動力不僅普遍而且強大,與此相對,那些無法成功啟動這個動力的人往往容易沮喪且缺少自信。
「我的」不一定就是「好的」,任何一個心智成熟的人只要稍作反思,都能得出這個結論。一般來說,人在年少時更容易成為一個「唯我論者」。其實不單是個體,民族同樣也如此。在不成熟的民族眼裡,這個世界只有兩類東西:我的並且是好的東西,以及不是我的因此也就是壞的東西。古希臘人將周圍的民族不加區分地一概稱為野蠻人,所謂Babarians,意思是說話時發出「巴拉巴拉」聲音的人。唯我論者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能跳出來看自己,如果希臘人意識到自己的發音在那些「野蠻人」的耳朵裡也是「巴拉巴拉」,興許就不會這麼地自信滿滿。
上世紀4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克拉克兄弟曾經做過一個研究,把兩個洋娃娃(一個黑人,一個白人)給兩個小朋友看(一個黑人,一個白人),然後問他們,想跟哪一個洋娃娃玩,哪個洋娃娃更漂亮更好看。不出所料的是白人小孩幾乎全部都選擇了白人洋娃娃,出人意料的是大部分的黑人小孩也選擇了白人洋娃娃玩,並認為這個洋娃娃較好。顯然,對於上世紀40年代的黑人小孩來說,「我的」和「好的」之間隔著十萬八千里,這種強烈的自我否定,以及想要成為別人的願望,正是自我認同出現嚴重失衡的後果。據說,「黑就是美」的觀念要到上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之後才逐漸在黑人意識中紮下根來。
「我的」當然不必然就是「好的」,但是如果反過來認為「我的就是好的」無非是敝帚自珍式的阿Q心理,又未免稍顯表淺。
法國大革命之前,英國人埃德蒙‧柏克曾經在凡爾賽宮親眼目睹過路易十六的妻子,當時的她「充滿活力、光彩和喜悅,猶若啟明星,璀璨奪目」。十七年後,這個柏克眼裡纖塵不染、完美無瑕的王后在「暴徒」的威逼中服下毒汁,柏克內心的憤懣可想而知:「歐洲的光榮已往矣,那種對名分和女性的耿耿忠誠,那種自豪的屈服,那種富於尊嚴的依順,那種即使在奴役制度中也能使高尚的自由精神不致失墜的心靈依附,所有這些,我們永遠永遠看不到了。」
顯然,柏克哀惋的不單單是法國王后的香消玉殞,更是那個屬於他的生活世界——如騎士精神、貴族生活等等一整套行為系統和情感模式——的煙消雲散。1927年6月2日,國學大師王國維在頤和園的昆明湖投湖自盡,陳寅恪評論其為「文化殉節」,所謂「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好的東西總是相對於一個特定的參照系,在人文世界裡,這個特定的參照系常常以第一人稱的形式出現——「好的東西」就是「對我(們)而言是好的」。「我的」與「好的」之間的關聯性,在柏克和王國維這些處於歷史轉折處的文化人這裡,顯然要比敝帚自珍來得更加深沉和厚重。
每個人都有許多張面具,個體的自我認同會隨著情境的變化而變化。一個哲學院的女教授在和中學閨蜜「飯罪」時,哲學家的視角會咕咚咕咚地往外冒;當她參加一群大老爺們為主的學術會議時,女性意識興許就會凸現出來;如果這場會議發生在法國巴黎,黃種人或者中國人的自我認同沒準就蓋過了女性以及哲學家。顯然,在所有這些身份裡,「哲學教授」是一個經過後天努力而獲得的社會角色,假使有一天她厭倦了學院生活,完全可以脫離這個身份。但是種族(黃種人)和性別(女性)這樣的社會分類,它們是被先天所規範的,而不是後天可獲得的,這樣的身份認同沒有出口可言,哪怕有人實現了事實上的脫離,比如邁克爾‧傑克遜,心理學家認為這種脫離在心理上也還是不可行。
在這個「黃種女性中國哲學教授」的所有身份認同中,最讓人為難的也許是民族認同以及國家認同,它們介於先天規範與後天獲得之間。曾經有人說,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什麼英國人、法國人或者美國人,我看到的只有一個個具體的個人: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實情真的如此嗎?以「東方主義」研究著稱於世的薩義德說,歐洲人和美國人的身份絕不是可有可無的虛架子,當一個人與東方相遇的時候,他一定首先是以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的身份進行的,然後才是具體的某個人。當然是這樣子。我有一個金融界的朋友,平均一個月出一趟國,每當提起在國外遇到不守規矩的中國人,都恨不能找一桶立邦漆把自己給刷白了,這種羞恥感恰恰反映出他對「中國人」難以擺脫的認同感——你永遠不會為了一個阿富汗人在第五大街上吐痰而感到羞恥。
斯特雷耶在《現代國家的起源》中說,在現代世界,最可怕的命運莫過於失去國家,如果一個人不幸成為「沒有國家的人」,那他什麼都不是——「他沒有權利,缺乏安全保障,幾乎沒有機會去得到有意義的職業。在國家組織之外,不存在所謂的救星」。但是這個狀況不是自古皆然,事實上,歷史上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不僅國家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句名言說,民族不過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可是問題在於,即使民族(國家)認同包含著神話和建構的因素,一旦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成為現實,人們就很難脫離既定的軌道。馬雅可夫斯基說:「我想讓我的祖國瞭解我,如果我不被瞭解——那會怎樣?那我只得,像斜雨一樣,從祖國的一旁,走過。」這話說得輕巧,但是在面對自己的故土家園,有誰能夠如此輕鬆寫意地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胡適當年痛感「中國事事不如人」,既然如此,不如削骨還父、削肉還母,再造一個真身,全盤西化;而中國本位論的支持者則反其道而行之,主張「凡是好的都是儒家的,凡是壞的全賴別人家」。如此截然相反的立場,歸根結底,仍舊是在拷問「我的」與「好的」之間的複雜關係。
時至今日,所謂「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之爭仍舊在延續這場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的主題。不久前,我的朋友劉擎說過一句特別點題的話:「對於探索中國發展而言,若一定要談論什麼模式,更基本和迫切的真問題是:什麼是好的(可欲的)模式?而以『我們的還是別人的』作為標準來決定好壞與否,是一種智識上的混亂。」這句話的有趣之處在於,它徹底否定了「我的」就是「好的」。姑且不論從「智識的邏輯」出發是否必然得出這個結論,若就「行動的邏輯」而言,劉擎的這個說法稍顯倉促。
當一個負面事件發生,比如汽車追尾了,戀人分手了,國家解體了,或者傳統文化衰微了,為求理解,人們總要查找原因。歸因理論的創始人海德認為,當事人和行動者傾向於訴諸「情境原因」——天亡我也非戰之過,總之和我沒干係;觀察者或者反對派則傾向於訴諸「氣質原因」——都是你的錯。行動者推諉責任,觀察者強加責任,說來說去,還是在和自我認同作鬥爭。
說到觀察者和行動者的不同,不得不提柏克的這句話,他說:「思想家應該中立。大臣卻不能這樣。」按照施特勞斯的解讀,這裡的意思是,大臣(行動者)必定對於「我自己的」東西有所偏私,這是合乎情理的——他的職責就是要站在自己這一方。而對於思想家(觀察者)來說,他要毫不猶豫地站在「優異性」的一邊,而不管它是在何時何地被發現的,也就是說,在好的與他自己的這兩者之間,思想家要無條件地選取前者。
現在的問題在於,在權衡比較「我的」與「他的」、「好的」和「壞的」這一類複雜關係時,我們的身份到底是什麼?觀察家還是行動者,或者乾脆二者都是?如果這兩種身份發生衝突,我們究竟應該聽命於誰?在我看來,「中國模式」的倡導者們過多強調了「行動者」的身份,不僅橫蠻無理地站在「我自己的」立場上,而且不加區分地把「我自己的」直接等同於「優異性」。另一方面,徹底割裂「我自己的」與「優異性」關聯的人則把自己想像成可以像上帝一樣擺脫任何特定視角的「觀察者」,而忽視了有一些「好」不僅是「對我而言是好的」,而且它們永遠都無法被還原成為一些中立性的指標和數據。
當然,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是,好的東西就一定「應該」成為我的嗎,好的東西一定「能夠」成為我的嗎?都說「兒子總是自家的好」,這裡面除了有偏私、有護短,還在於兒子打得罵得換不得。
海德格爾說,人是一種「被拋」的存在者。生而為中國人、德國人、美國人、利比亞人,只是一個純粹的偶然,自主性在這裡根本不起任何的作用。然後,你在如此這般的家庭氛圍、如此這般的傳統文化、如此這般的價值世界裡逐步成長,然後有一天,你擁有了理性的反思能力,你發現過往的一切不僅有美好,也有謊言、欺騙、愚弄和神話。你意識到上帝雖然像投擲骰子一樣隨機給了你一個身份,被拋者仍然可以對於「我是誰」做一個理性的決斷,就像處在夢魘中的人那樣,掙扎著讓自己翻一個身,或者用自己的意志把自己喚醒。可是我相信,總有那麼一些東西,在智識的邏輯上你也許認為它不是那麼的好,但是在行動和情感的邏輯上卻永遠無法像割除闌尾或者扁桃體那樣,輕輕鬆鬆地一刀了之。
去年我去威爾士的首府卡迪夫,坐在陽光燦爛的海灣邊上喝咖啡。朋友抱怨說,這個海灣怎麼不一望無際?為什麼沒有沙灘?又說卡迪夫只有一個很小的廣場,到處都是破舊的房子還有呆板的面孔。這讓我想起《殺手沒有假期》裡面,那個年輕的殺手最初也是這樣抱怨的,最後他愛上了布魯塞爾那座小小的、破舊的城市。
和一種文化,一座城市,一個人,一條狗,一本書,一首曲子……建立起關係,需要獨特的現實感知力和歷史因緣性。正是這種無法被量化和還原的特殊記憶讓我們成其為我們,讓我們瞭解那種只有我們才瞭解的好。
(20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