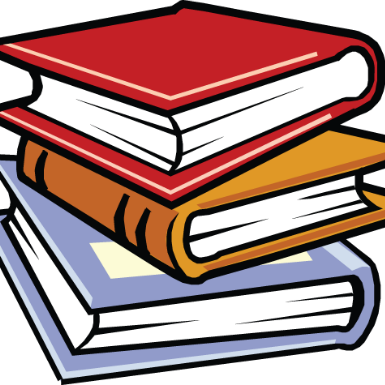「木匠是民之本」,中國人對木頭有著極為特殊的情感。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在用遠比石材脆弱很多的木材建造家園。生活在樹木旁,住在木房子裡,在木桌上吃,在木床上睡,用木頭造紙,用木頭刻版印刷。五行之中,「木」給人的感覺是最親切的。
木器組位於西三所進門第一個院子,不知是否因為「木」的獨特屬性,這個小院裡的樹木是最繁茂的。夏天時,它們的枝杈在天空中連接起來,綠蔭遮住整個庭院。
中國傳統傢俱的最高成就出現在明代。多採用黃花梨、紫檀、鐵梨等名貴硬木材,少有繁複裝飾,運用木材的天然色澤、紋理,以各種直線、曲線的組合來達到簡潔大方的裝飾效果,「材美而堅,工樸而妍」,被稱為傳統傢俱的黃金時代。清代傢俱在此基礎上予以發揚,用料厚重,雕刻繁瑣,裝飾華麗,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明清硬木傢俱的收藏與修復是故宮博物院一個極具特色的專業領域。明代隆慶時期,為開闢稅源而開放海禁,允許私人海外貿易。這一舉措直接促進了傳統傢俱黃金時代的到來。南洋各地盛產的貴重木材源源不斷進口,製成硬木傢俱後,又成為重要的出口商品。它和瓷器、漆器一樣,都是我國傳統的外銷商品,對銷往國外的工藝品也產生顯著的影響。15硬木傢俱流行,皇室更是當仁不讓,這種新流行的材料結合皇室要求就形成了明式宮廷傢俱。宮廷設御用監,「凡御前所用圍屏,床榻諸木品,及紫檀、象牙、烏木、諸玩器皆造辦之」,專為皇室製造宮廷木器。清朝繼承了明朝的規制,設造辦處,又從全國選調最好的工匠進京,形成了特有的宮廷木器修復技術。
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高春秀調入故宮負責木器文物的整理和修復。當時故宮古物館設裝潢科,僅有少數人從事小件硬木器、書畫裝裱與鐘錶的修復工作,這是故宮博物院最早期的文物保護工作。解放後,相繼又調入了胡秀峰、王吉友、王慶華、白錫來、史建春、趙福水,成立故宮木器修復組。如今故宮木器修復室的老師傅有兩位就是子承父藝。在最大限度保留木器傢俱原有信息的文物修復理念之下,這些高手們的技藝在日復一日的文物修復中,交流融合,代代發展。
木器文物修復遵循「不改變文物原狀」原則。例如,明式木器的特點在於面板相交處採用龍鳳榫結構,傷況多是榫片劈裂或折在槽內,在修復中不能只顧外表不顧其榫卯結構。榫卯結構是修復、研究的重要一環,否則,雖表面上看不出來,但已改變了文物原狀。另外,對文物原件的殘損部分的取捨與複製是「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又一焦點,這是修復中最常見,也是最難把握的。故宮木器修復師郭文通的原則是:「要千方百計地使出渾身解術保留原文物的殘件,慎之又慎,盡量減少複製部件的範圍和數量,以保留古文物的原內涵。」他將一個碎成六十多塊殘片的金漆嵌玉宮燈修復到完整如初,整個過程基本沒有用新的材料,僅以原件中銅絲的彈性與韌性黏合殘片,完成一個造型面後黏結其他幾個面,最終達到完全保留原件,完美體現了「不改變文物原狀」的修復理念。
木器工作室以各項木器製作技術為基礎,結合最大限度保留文物價值的要求,遵循原風格、原工藝、同質材料的匹配方式,對故宮木器文物進行日常護理和損傷修復。修復的基本流程為:清理污漬灰塵,記錄傷況,查閱資料,分析工藝特點,制定修復方案,之後才能動手修復。比如補配的活兒,首先確定要配哪裡,找出同樣類型的原件進行拓樣,再找同樣的材料把拓樣放在上面,把配件的外形鎪出來,接著進行雕刻,雕刻後的物件要比照原件反覆調整,直至完全契合。最後是打磨、組裝、燙蠟。




魚鰾膠,沿用千年的粘合劑
許多手藝人不善言辭,更不擅長理論。在《故宮博物院文物保護修復實錄》一書中出現的師傅們的文章,大多樸實無華。文章起首通常是描述修復物品,結尾往往是「一件完好的某某某,就呈現在我們面前了」或「修復工作圓滿結束」,但拙於言詞的他們寫到工藝規範卻細膩動人。以木器組劉國勝師傅修復明代黃花梨圈椅為例,他記錄的「磨光」程序為「先用細砂紙輕輕打磨,再採用傳統方法用銼草進行打磨。銼草也叫節節草,是一種天然植物,用熱水泡軟後,用竹籤穿入草的空心裡,手持竹籤進行打磨,這樣圖案所有部位都能均勻磨到。多次反覆打磨之後,雕刻圖案會變得非常光潔、細膩、圓潤,產生年代久遠的感覺」。老話講「三分雕,七分磨」,打磨很吃功夫,功夫在現代成為武術的代名詞,但在以前,它指的是時間。有的木匠用砂紙、動物毛皮打磨完了,最後用自己的手細細摩挲木件,以他們粗糙而溫柔的手掌磨掉木件上最細微的毛刺,在木件表面產生一種包漿的光澤。這個過程中,匠人最大的技巧是一顆沉浸其中的心。
修復中必須遵循 「原風格、原工藝」,就算有的藏品工藝水平不高,甚至,按修復者的審美來看簡直是醜陋。這曾經是木器室現任科長屈峰的痛點,他沉痛地說並不是老的東西都是好的,有些老的東西很醜。最初修到這樣的器物,他總有種衝動要改造它們,但這是文物修復大忌。哪怕是價值不高的工藝,「但它反映的是某一特定環境下的製作方式,體現著時代風格,要尊重其本來面目,在修復中把它的整體風格作為參照物,避免人為地、想當然地錦上添花或畫蛇添足。」 16老師傅郭文通的這段話,簡直是針對徒弟屈峰的告誡。
進故宮後,按照故宮文物修復的「師徒制」傳統,屈峰拜組中年紀最大的郭文通為師,在全組同事面前,雙手敬茶,喊了聲「師父」,開始之後的三年學徒式訓練。但以學院一等獎研究生畢業的屈峰最初並未進入工匠心態,而是以藝術家的眼光去打量手上這些清宮用具,對其裝飾的繁瑣不以為然,但幹活還是利索,每次都是早早交活。一次給一個玉山子底座補配缺失的底足,他一口氣做完交活,師父說:「你做快了。」快了不好嗎?「這東西你琢磨過嗎?」聽到這句話的屈峰愣住了,好像被點了一下。
另一次是修復文淵閣的一扇圍屏,三塊雕龍板缺損需要補全,屈峰領到一塊方形的小雕龍板,對於科班出身的他這都不算活。雕到八九成時,屈峰瞄了眼旁邊劉師傅的團龍板,發現不對,兩龍對比美醜立判。劉師傅指點他:「你這龍跟沒吃飽似的,身上的曲線不夠順暢,顯得沒有勁兒。」同樣一道線,中間的軌跡、力度和律動的變化,都需要沉下心,反覆琢磨。這是工匠的智慧,是匠人千萬次重複後達到的自由之境,外在表現是他們創作時的得心應手。手藝人用手直接創造,從心到手絕無分離,也不容分離。雖然他們不擅長理論,但美的法則早已體現在他們手上。
對於屈峰,這是一次重新審視工匠世界的機會,「在這兒最大的獲得是磨性子,」不管來的時候是什麼人,心高氣傲也好,飛揚不羈也好,進故宮的年輕人都會經歷一個「磨性子」的過程。在故宮待了十年以上的年輕修復師,氣質跟新來的人是不同的。很難描述那種不同,他們走路的樣子更沉穩自信,那種自信,是熟悉了文物修復中的條條框框、接受了界限後獲得的一種自由,是千百次重複做一件事情後帶來的具體的信心。現代社會中的成功者離自己的創造對像通常遙遠,所謂成功常常是銀行中網絡上瞬息萬變的數字遊戲,手藝人的自信卻誠實而具體。有時候,屈峰也管這個過程叫做修行。

修復完好的菩薩像
被磨過性子的屈峰仍然保留著藝術家的趣味,在工作室角落裡雕一個愁容騎士王小波,在院裡放一個自己雕的胖墩墩的蘇東坡,兩個都是自由不羈、特立獨行的文學家,這是他的抒情。但他也會熟練地運用木器室訓練新人的傳統方法,讓他們砸魚鰾,以此來磨煉他們的心性。魚鰾膠是木器組的秘密武器,每隔一兩年就要去海邊千里迢迢買回來黃魚魚肚,用溫水泡發、加熱,放到鐵鍋裡捶打,直到打成糊狀,過濾晾乾後裁成手指粗細長條,用時加水熬成膠。砸膠是最痛苦的,被捶打搗碎的過程中,出了黏性的魚鰾會把整個鍋都帶起來。「木器室裡年輕的小伙子輪流著一刻不停地砸,一天下來,頂多能砸半斤的魚鰾膠。所以老話叫好漢砸不了二兩鰾。」整個製作週期長達數月。木器組王師傅的父親,當年修太和殿龍椅時用的就是這種膠。鍋裡一熬,拿根筷子插進去,拎起來都不往下滴湯兒。最關鍵的是,用這種膠修文物,完全可逆,用點熱水一泡,就能化開。
砸魚鰾膠,屈峰幹過,他的師父郭文通幹過,郭文通的師父白錫來也幹過。民間手藝的秘密就包括在無數類似這樣的千錘百煉中,其間並無捷徑—他們不用市場上現成的,因為不如自己做的效果好。手工藝做到一個境界,對工具輔料的要求就越高,以至於只有工匠親手做的才能滿足要求,因為親手做的物料裡,匠人用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