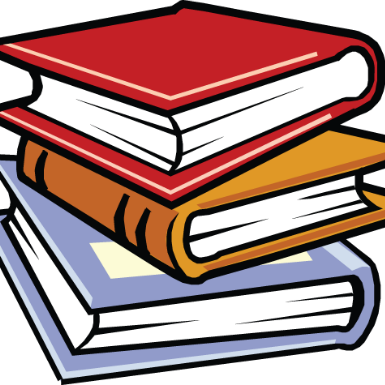我是清華美院畢業,2011年來故宮的,到今年五年了。我們這邊都是師承製,沒有儀式,但是有制度,老師會做一個規劃,部門裡面會給老師一筆費用。對,我是叫老師,還是像上學一樣。
剛進來時,印象最深的是基本技法的練習,尤其是勾線。我在美院讀的也是中國畫專業,這些基本技法應該是在上學期間已經解決了的,但是故宮對專業技法要求特別高,要重新練,當時勾了將近一年的線。所有畫畫的人都知道,勾線的練習非常重要,它是一個基礎,底子打得有多厚,做的建築才能有多高。但是很少有人真正拿出一年時間去勾線,在學校要安排其它的課,生活中有其它的事。但是在這邊,這就是工作。
美術學院是開拓創作思維的,臨摹是為了學習技法,學習古代繪畫的精神性的東西,是為了創作。這邊臨摹,要求高精度高準度,一模一樣。高校的標準可以讓你畫國畫沒問題,但那個標準拿到這邊來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來了之後有幾個月一直在勾線,這個過程讓我感觸很多。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做一件簡單的事,手和心結合做這麼一件簡單的事,我們對勾線這麼一個簡單的行為,就掌握得更微妙了。比如它的水分多少,摩擦力是什麼摩擦力,墨的顆粒的粗細,在什麼樣的紙上能產生什麼樣的效果。掌握這些微妙,也就提高了對畫面基本元素的掌控。這種標準,高校那種訓練方式是遠遠達不到的。
臨摹也有自己獨特的訓練方法。我們練線時是在膠板上勾,是一個塑料的透明狀的小薄板,表面光滑,加上墨是液體狀,毛筆又是濕潤狀態,都是很滑的,在這上面如果都能勾得很好,再換成紙,勾起來就比較簡單了。胡老師他們都是這麼訓練過來的,確實是一換到紙上就特別簡單,特別輕鬆。它訓練的是你手腕對力度的掌控、協調。
要摹好古畫,摹畫師就要有那個時代的功力,這個要求並不苛刻。我們的工作不僅僅要臨摹,還要接筆。接筆就是檢測一個人的綜合審美素養、對基本技法的掌握,就是在考驗一個人。臨摹是用自己的能力、方法去達到這個標準,而接筆是直接跟標準碰撞,直接進入角色。它要求更高一些,這個機會也很難得,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做的。
第一次為文物接筆的時候,沒有緊張,可能也會有一些,我覺得還是得益於我們這個系統的訓練,就是心裡有數。那是我來的第三四年吧,因為我們三年是一個培養階段,培養階段是不動文物的。這也是對文物的一個保護。
對,前面已經有了四年的高校學習,仍然要一步步地接受學徒式的訓練。只有來到這邊,見到這個標準和要求之後,才知道原來在最基本的繪畫語言上還有這麼大的差距。所以是不著急的。而且經過那種系統訓練,你真的覺得自身得到了很多。後期上手去做就不是很緊張。因為前面三年已經練了很多了。

在這邊每天的工作,如果畫畫的話,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磨墨。我們不用現成的墨汁,研出來的墨,首先它穩定性比較強,裝裱時不會跑墨;畫完後要洗硯,當天的墨當天用。如果它過了夜,我們稱為宿墨,宿墨的膠體有的就揮發了,剩下全是炭化的顆粒,它的穩定性差一些。
磨墨的技巧就是用力盡量均勻。用力均勻,磨出來墨的顆粒大小差不多。如果你特別使勁,磨出來的墨可能比較粗;如果太輕,又磨得太慢,而且顆粒比較小。當然從畫畫效果上來講,要求墨盡量細。如果墨很粗的話,你想畫得很細是不可能的。所以說中國畫,就要創造繪畫過程,從頭到尾這個工序都要很講究,它是修心的過程。磨墨是畫畫第一步,它不僅僅是製作墨汁的過程,它是人從生活狀態進入創作狀態的過程,磨墨就是在靜心。
不僅磨墨,前期的這些基本功訓練,都不僅是技法的訓練,還是狀態的調整。在高校的狀態是不一樣的,我們接觸的都是老師,還有身邊一些畫家。老師要做市場,有很多涉外活動;而我們是作為畫家或後備畫家培養,同學們在一起,能力都不錯,會彼此競爭,比如會涉及到獎學金等利益關係。
外面是在各種利益關係之中生活。到這邊那些就沒有了,沒有人去強調利益,很和諧。我來的時候這屋還有四位老先生,都是女同志。我一來大家都把我當孩子一樣。這邊就像一片淨土,狀態很純粹。因為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做一件很簡單的事,看似簡單,但又非常重要。追求利益的心態一下就靜下來了,反而更接近繪畫的本質。在這種狀態下感受到的東西,才是最微妙的。
我反覆說微妙,具體到技法,就是對力度、水分、材料,我們能夠掌握到很小的微差。掌握不好,那就談不到畫得好不好,你只是一帶而過。其實哪怕是一條線,那也是有精神性,有氣質的,不是說我們把這個東西摳出來就行了,而是真正地感悟到,盡量用原作者的那種創作狀態感悟,進入他的狀態,這樣出來的作品才可能和原作的精神狀況相通。
在美院我們是作為藝術家培養的,但這和作為臨摹師的職業狀態並無衝突。相反,因為我是學創作出身,接筆中,它缺的是什麼,原作者是在什麼狀態下,什麼審美思路去創作,這方面我就相對敏感一些。另一方面,臨摹不會損害創作。臨摹自古以來就是創作的一個過程,基本功紮實了,看古畫,有價值的信息看出來會更多,因為我們經歷了高標準的訓練。所以說這種學徒式的基本功的訓練,對學院出來的人是非常有幫助的。
單位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做臨摹時一般停掉創作,因為臨摹要高度地尊重和遵循原作。不像兩宋是共性審美,後來美術史是朝著個性審美發展,如果長時間搞創作,可能在臨摹的過程中會有障礙。我倒是沒有停掉創作,因為在我心裡有一個界限,盡量不要把自己的個性帶入到臨摹的畫作裡,還因為我搞傳統方向,其實大部分時間研究的是共性審美。
同學中的確也有搞創造不錯,名利雙收的。其實搞專業的人在一起,更尊重的是對方專業上的含金量,而且雙方也是清楚的,大家還是更看重這些,其它的都是表面的。因為我們是屬於直接接觸文物的部門,我們看到的這些經典,外界的朋友或是同學,他們可能一直沒有機會見到。看到真跡對學美術的人還是重要的。畢竟都是專業院校出來的,大家很明確地知道什麼是從大道,什麼是從小道,什麼是尚大美、什麼是尚小美。當然還在持續交往的朋友也會有著相似的精神追求,尤其我們這個年齡,最要緊的還是積累和學習的狀態。
我是1987年生人,今年二十九歲。我覺得現在就應該是積累和學習的狀態,如果現在就要如何如何,一方面是過於求成,另一方面本身技術還不好,你前期不紮實,後期通過其它手段,就是做起來也是不穩的。因為我們這個職業就是經過長時間的積累,最後產生質變,產生昇華。最近這兩年外邊的市場也不好,也在調整,大家越來越理性地認識藝術品價值,不像幾年前大家都跟風去做市場。許多畫家也都收回來畫精品,挽救他的市場。但是我覺得就應該是這種狀態。
這可能和我一直主攻共性審美也有關。共性審美從概念上講就是大美,比如兩宋的審美幾乎包含所有的審美元素,畫面的裝飾性、色彩的協調、筆墨的精進、氣息的飽滿張力等。元以後為什麼不那麼畫了,因為太累。最後變成大家一進這個領域就緊張,因為要包含這麼多的元素,它是一個幾近完美的東西,所以不能釋懷了。釋懷就是通過一種行為達到我內心的寄托和愉悅,我要搞審美輸出,我要讓別人感受到我的這種狀態。兩宋時大家追求的是創作這幅作品我很舒服,別人看了也舒服。但個人審美發展到最後,極端的就是,我自己舒服,你們舒不舒服我就不管了。
元代文人畫興起,就是在共性審美的高壓下,覺得自己要釋懷一下,要舒服一點。我是覺得呢,我們這個年紀應該把共性審美的東西系統地積累一下,我們看元明清這些文人畫,他們其實都是具備強大基礎的。沒有基本功,也是無法直接就釋懷的。
我覺得畫畫是一個事業,做規劃的話應該做得遠一些。
臨摹是以臨摹工筆畫為主,最多到小寫意,大寫意就不臨摹了。但是即使是工筆或小寫意,也要追摹原作者的創作狀態。現在有很多人理解,工筆就是要畫得細,但沒有神韻,其實不是。古人可能對寫意和工筆是沒概念的,這是後來人的總結。不應該抱著這種區分去畫,容易把簡單的東西用更簡單的方式去畫,複雜的東西用更複雜,甚至用製作的方式去做。
簡單的東西用更簡單的方式去畫,就是說如果心存了這個概念,我畫的是寫意,你會想簡單地畫畫。其實畫寫意也要有很好的基礎,因為雖然表現形式是簡單的,但要用簡單的方式表現出更多的內涵,這是寫意畫的宗旨。
複雜的東西用更複雜的方法畫,就是提醒自己畫的是工筆,我應該畫細一些,畫精一些,使勁往裡畫,最後可能就把一些製作性的東西加進去了。我看現在有很多工筆畫用些特殊材料,用一些製作性的技法,橡皮擦什麼的,做出一些特殊效果。我覺得它只是在追求一種質感和物象而已,並沒有把更多的審美元素通過畫的方式表現出來。製作可以進入到繪畫的語言裡面來,但這種涉入、借鑒和學習是有尺度的。就像我搞臨摹工作,創作怎麼搞,是有一個尺度的。其實古人更強調「畫」這個概念,強調畫的過程和動作。現在好多搞工筆的畫家用太多製作,反而失去了繪畫本身的語言和味道,很容易就變成裝置藝術。

巨建偉在臨摹
也許有人會覺得我這樣的想法有一點落伍,但我覺得學習、傳承和發展繪畫藝術,應該站在一個歷史的高度。第一,要真正地熟知傳統;第二,要客觀地面對現在這些審美元素,客觀研究非繪畫語言的借鑒和學習;第三,發展也是站在傳承的角度去發展。如果先人幾千年來的審美歸類、我們民族的審美優勢都不要了,直接去拿別的文化的審美去做的話,這是失去了最重要的東西。因為我們的思維方式是在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下成長起來的。
故宮畢竟有自己的節奏,很多剛進來的人有一個磨合的過程,我現在是過渡階段。我來了之後,深切感受到有更多的東西需要學習。同時,一個完整的審美是構建在不同方面的,是一個綜合領域。我們這邊什麼部門都有,不僅在自己的古代書畫上學習,而且能夠看到其它的領域,拓寬審美,這種吸引力更全面,比一個學科、或一個專業更具有吸引力。所以對單位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就像一個人對學校有情結。
另外一個方面是人際關係,大家都很熟,在不同的專業和領域有自己的成果,溝通過程中又能彼此學習。不僅是跟文物學習,人跟人之間也有這種學習,這幾點因素造成了我們對這邊的高度認同。
雖然如此,可能因為年輕,所以也是在不停地調整。我們最好的狀態就是不受任何影響,全身心地在這邊搞研究。但除了工作之外,還有很多其它的事,和我們搞專業矛盾的東西……其實就是一些俗務,但它會佔用我的時間,最重要的還是時間。
臨摹的確面臨著電腦噴繪的衝擊,會不會感慨自己進入了一個冷門行業?所謂熱門冷門還是跟利益有關。不熱門有可能是暫時的,但是這個技藝,或者說傳承是恆久的,因為繪畫本來是文化傳統裡很重要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掌握古法,掌握這種傳承的責任,它冷不冷熱不熱的,沒什麼太大關係,就像古人講的,朝聞道夕死可矣,我知道這個東西了,我那種滿足感和我那種成就感是那些東西沒法衝擊的。所以沒有這樣的感慨。因為我們不用這個東西跟別人做生意,也不拿這個東西跟別人去比擬。
來這裡五年,臨的作品並不多,幾件吧。因為我們中途可能還會協助他們去做接筆,做些其它工作。接過的畫中最喜歡的是《崇慶皇太后八旬萬壽圖》。裡面有兩個皇子,面部只剩下一半,比如有的就剩一隻眼,那邊就得畫出來。接筆就是這樣,要通過現有的一些信息,然後把另外損失的信息補上去。因為那個留下來的信息量不多,而且面部接筆比花花草草更難,我比較喜歡有挑戰性的工作。
現在臨摹的《羅漢圖》是我喜歡的。我喜歡宗教題材,因為有很多非現實的的故事情節、人物或者畫面。長時間畫現實的東西,會比較壓抑。畫一些我們認為好的畫,又能在裡面寄托思想,寄托我們的情感,畫面給人感覺是可能存在的,在現實中卻並不存在。這個空間和領域是我比較喜歡的。
工作對我的創作主題發生了影響,現在朋友聚會,也會酒後即興地去畫羅漢圖,它既是一種自覺的主題創作,也是不自覺的潛移默化。因為長時間地沉浸在精神的享受中,所以當我去釋懷,把這種喜悅分享給別人時也是這種狀態。
對,臨摹對我一直都是一種享受,因為你做的事讓自己每天都在進步,你有成長感,有向上的感覺。不像有的工作,下了班都不想提工作的事,因為那個過程對自身可能沒有什麼滋養,所以他也不會幹得太好。像我們這種工作你永遠都覺得自己很舒服。
這幅《羅漢圖》我從去年年初接到,之後馬上就做文物修復成果展,做了一年左右。真正在摹有七八個月,摹完大概要一年吧。你說得對,照相一分鐘可以照六十張,但是一個臨摹師一年只能臨一到兩幅。臨摹比自己創作要慢,因為自己畫是按照自己的規則在做事,臨摹是我們按照別人的規則去做事,思維狀態、各個狀態都是在調整中去進行的。所以效率要低於創作。進來四五年,就只臨摹過幾件。聽起來比較少。

清 丁觀鵬《羅漢圖》
這種節奏跟外面世界迥然不同,但是走到外面時倒沒有你說的那種不適感。對一個搞藝術的人來說,他區別於其他個體,比如商業個體的,就是他能夠在自己的世界裡面去成長,去生活。因為他是給別人創造精神世界的人,如果自己的小世界都那麼脆弱,那我們就沒有能力去營造別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