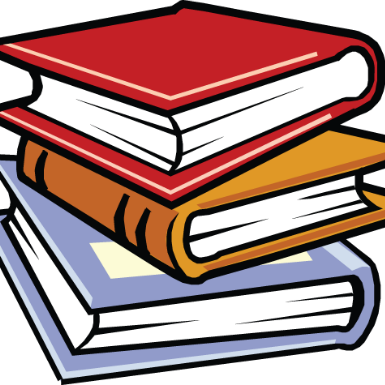我是1980年2月份來的故宮,當時我十八歲。我們都是故宮子弟。我爸是1954年河北軍區轉業到故宮,我姥爺也是軍隊的,那時候沒有宿舍,就在故宮角樓兩邊,東角樓西角樓河邊蓋工人宿舍。宿舍在城牆外頭筒子河以裡,兩邊都是故宮的職工子弟,等於從小就在故宮這兒摸爬滾打。小時候就覺得院子挺大的,後來幹了這個,覺得它太深奧了,越來越覺得它深不可測。
我高中畢業就上故宮干臨時工。後來故宮跟英國簽了合同,英國定了一批青銅器,所以1983年來到科技部。剛來時,我記得特清楚,趙師父先是讓我看廠規,看了一兩天,然後給了一把豎的刮刀,就讓你先去刮那個銅,其實就是練性子。因為這工作需要坐得住。那時覺得,天天刮這個幹嘛,也沒多大手藝。他就讓你坐下來踏踏實實去練性子,能踏踏實實地掌握。

後來就慢慢開始跟趙師父學做舊。先看,然後一點一點修小件,從小活兒練起,後來就開始進行複製。那時候人比較豐富,這組的人員比較旺盛,都是年輕小伙子,幹勁也高。
一開始上手都是資料,後來才慢慢承擔一些重要的。那時候故宮每年有一個文物精品展,有時外地送來一些青銅器,比較破,就跟著師父一塊修了。因為精華展,送的文物都比較有代表性,一級品比較多。展完了也修完了,他們把完好的成品拿回去。這對我們是個很大的鍛煉。
馬踏飛燕應該是1971年修的,聽別的師傅講,出土時,馬鬃好像缺了點,脖子那兒有七個洞,完了馬尾巴是斷的。這種東西是要找平衡的,就說你要讓它站穩。就說鼎吧,比如說那鼎缺一條腿,我不能光焊上了,必須用手測一下它,像我們一般就拿一個平的東西擱在上頭點兩點,看平不平。能立住了,才能四周全焊了。這是我們修復的一個技法或者方法,就是得找平,你不能修完這東西,翹著,那屬於手藝沒到家。
當時馬踏飛燕好像是礬土掉了。原本那裡頭注礬,礬土一掉可能空,空就晃,後來給它填上了,重心找到就穩了。
趙師父給我的印象就是一樂樂呵呵的老先生,隨和,對人比較謙和。那一代的老先生好像都是這樣的,都比較謙和,見面說話沒有什麼架子,但對活兒是嚴格的。趙師父一般收活,「再鑿吧鑿吧」,就是說你沒弄好,可能你做得有點新,剛做完那個火氣還有點大。我們有一道工序叫咬舊,得把那個工藝咬下來,他可能再加點土。師父的做舊水平相當不錯,感覺特別好,他往那兒一坐,盤著腿,一坐一上午,一坐一個下午,真是挺深功夫,真是坐得住。
趙師父對技術要求比較高,你要做好了他也高興,你要真做不好,他有時候也真著急。但是非遺的東西,怎麼修得更好,需要你有一個悟。它裡頭那銹,我們叫生坑熟坑銹5,半生坑半熟坑,鑿坑水坑6,這是我們所說的銹的名稱。有的你摸著它,什麼銹沒有,但是裡頭跟銹的顏色非常豐富。做舊既需要傳統的做法,也需要有化學的技術。它不像仿製,仿製有時候就是大概形差不多,複製要求更細一點。趙師父對技術要求挺嚴。
我覺得手藝是現代機器代替不了的。不拿青銅器說,咱就拿玉器說,現在有機雕,你看機雕雕出來,和人雕出來不一樣。人雕出來就有人的思想,代表著人的哲學思想,或者理念。咱就常說看著朱曉松刻竹器,刻竹房子,你就看他的雕工,你能領悟到他的思想,這也需要你有一定的文化,你才越看越深,越覺得,厲害也好,叫敬畏也好,我覺得手藝就這種東西,你看了絕對特服氣。你看前兩天咱們這兒擺那一件,你仔細看,它那腿它那身子,那個鑽工,那個質感多厲害,活靈活現的。就跟畫畫一樣,有的人把這鳥畫活了,有的人把這鳥畫死了,它就是少一點東西。咱們做舊的時候,有些東西沒法準確說,比方說,這個舊我加一點紅加一點黑,我沒法用準確的刻量度跟你說,加一錢加一分加一兩,我要這麼告訴你,你加這個東西還是不靈。有時候就是經驗上的一筆,這一點一點變出來就是這東西,這就是經驗。我稀釋劑和顏色的配比和膠的配比,那個全是經驗。你說做那高銹,你做那鑿坑銹,鐵箍銹對吧,你怎麼做,兩個完全不同的銹,我用的東西可都是一樣的,但我用的手法不一樣,出來那銹就是不一樣。就是技術裡頭,它裡頭有手法,怎麼弄,出來鑿坑銹了,怎麼弄就是生坑銹了,這都有技術。自己得動一下腦子,琢磨琢磨這東西,怎麼做得像。你像夏商周的銅器,它那銹是一層一層的,它是套的,有立體感,你不能說我噴完一層,我再噴一層,給它全開了沒有層次,沒有一年一年過來的感覺,沒有歷史感,對吧。所以我們趙師父老說做得自然點,他說的自然我覺得就像這三千年,你得把那感覺,把那銹做出來就能逼真。趙師父做的活兒,那時候就是能讓一般的人打眼,這就是手藝。能做到這份上就是手藝。
最痛苦的時候,就是這點活兒在中間的時候,沒做成。等你完全修復好了之後,心情是比較快樂的。這件東西,拿出來是歪的也好,擰的也好,斷的也好,爛的也好,通過咱們自己的手,去把它一點一點地修出來了,這時候你是最快樂的。
中途肯定要遇到那些你要解決的問題,這時候是比較痛苦的。你得想方法,你要整形,你得想法怎麼給它拼接上,怎麼把它的型立起來,你不能混了。你還要保護文物,你不能再毀壞了,盡量保證別造成二次傷害。那時候是比較痛苦的,需要去思考,需要你仔細去琢磨,想辦法給它解決了,解決完了就是快樂。
這是個慢慢的過程,剛開始就是把手藝學到手,談不上什麼覺悟,也認識不到。但是故宮的東西不要拿,故宮的東西不要沾,這是老一輩傳下來的。這些都是從小就潛移默化,所以對文物保護的理念這根弦是沒敢鬆過,但是你說認識肯定是一點一點地在加深。
時代在變,修復技術裡也會加入科技,這是應該的。我1995年去陝西考古所參加(國家)文物局和陝西文物局合辦的中南文物培訓班,那時我們這邊沒有X光,那邊德國人已經使上了。我們修的東西,你從表面看,就是一銅疙瘩,但是用X光去照,裡面清晰地出現半兩錢的樣子。所以我們修時,按著那張照片,一點點地把它上面的銹剝離,一點一點地就是一個完整的半兩錢。這是很好的科技,通過照X光片,你發現裡頭還有字呢,再去銹,就明白了。但是一定要慎重,盡量用成熟的理念。

待修復的銅器
老規矩,干文物的不能有文物,所以以前老人是不讓你沾文物的,尤其是本行的東西。現在隨著社會開放,你可以喜歡一點,可以有自己的娛樂。我是對書畫比較感興趣,平常自己也畫兩幅畫。
我覺得文物修復就是這樣,他要真喜歡,你可能趕都趕不走他。不喜歡也挺好,不喜歡你硬逼著他幹,他悟不到,對雙方都是損失。社會現在開放了,他既然想幹別的,那就幹別的,他喜歡的東西肯定能幹好。我自己的孩子也不學這個,他現在在英國留學,學經濟。現在大了可能有點興趣了,以前都是「誰要你這破爛,你這破破爛爛,天天一堆」,現在大了,可能慢慢對這些東西感興趣了,但他不會再幹我們這行了。他現在對金融比較感興趣。
我這人就喜歡靜,能獨處。踏實了,能坐住,你才能做這個。這顏色,有時候你調一天,調兩天,這色你就找不著;有時候興趣一來,你找到那色了,一上午特別快,因為你已經完全進去了,趁著那感覺,趕快的,就跟畫畫一樣,坐在那兒畫。那種感覺到了,你是停不住的。你一停這思路斷了。
我覺得你要真能坐下來的時候,那就特別放鬆。琢磨的時候,痛苦。東西拿來之後,先把它看透,因為這銅器,在這塊兒可能有銅,在邊上就沒銅,你夾的時候就容易夾斷,所以你一定要看透了,該怎麼修,自己在腦子裡面形成一個方案。先哪步再哪步,一步一步的,這樣就對文物保護比較到位。做這個東西得悟,就像畫一樣。在我們這兒顏料畫筆都有,顏色給你你畫去吧,你也畫一朵牡丹,不是那回事。做舊也一樣,它顏料、膠這些東西怎麼配比,怎麼能做出銹色來,怎麼能做出幾千年的感覺來,這都得琢磨。非遺的東西就得靠腦子,好多東西是不能具化的。
難嗎?難你也是從頭干到尾,就是一個工作;干的時間長了,也不見得那麼神秘。就是有一個,說白了就是有個自豪感。因為你承載歷史。
好像是王世襄,他說初學的人去拿這把椅子,可能提著。對於王世襄那種人,或像我們向王世襄學習的人,可能是抱著這椅子去的,他視那文物為生命,他理解是不一樣的。趙師父那時候就說,聞著這青銅器有香味。其實你說有什麼香味,就是一種感覺,他就覺得一聞到那種「這就是老氣」,就是那東西就對了,他就是一種感情在裡面。你像趙師父1931年開始,干了將近七十年,他能沒感覺嗎?就跟那時候有人說的,說故宮是塊玉,不能隨便弄。扯遠了,你說故宮這兒全是磚,哪兒來的玉,他指的玉不是你理解的玉,你得達到他的程度,你才能感覺到他的。他說的是一個整體。每個人的理解,到什麼位置理解什麼樣的東西。
現在咱們通過幹這麼多年,對這些老先生的理念就開始理解了,覺得他們還是敬畏心比較強,我現在就是在學那種敬畏心,一定要有敬畏心。你想人家青銅器,一代一代傳了兩三千年,多不容易,咱們去怎麼給它傳承,你完整傳承三千年或者兩千年。修的時候,你想想你的任務多大,對吧,你修復好了能傳承三千年,你一定要懂這個文物,懂得它的價值,這才有傳承性。
註釋
3.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器圖典》,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
4.地子,指銹下面貼近器胎的腐蝕層。銅器由於入土時間不同,含銅量、土質不同,表層自然產生的色彩也不同,主要有黑漆古、綠漆古、水銀浸、皮蛋青、棗皮紅等。李震 賈文忠主編《青銅器修復與鑒定》,文物出版社,2012 年。
5.生坑,指新出土的器物,或出土幾年但器物表面未被灰塵、油污污染,也未做過任何人工處理,尚保持新出土時的狀態 ;熟坑,多指傳世的銅器或早期出土的器物,傳世經常賞玩,器物表面因手長期摩擦呈現光熟狀態,或者將新出土的器物上蠟擦光,統稱為熟坑。熟坑銹較生坑銹易做。李震 賈文忠主編《青銅器修復與鑒定》,文物出版社,2012 年。
6.水坑,像從水坑中撈出來的一樣,器物表面顏色漂亮,或湛綠湛綠,或黝黑黝黑,主要在長江以南地區。李震 賈文忠主編《青銅器修復與鑒定》,文物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