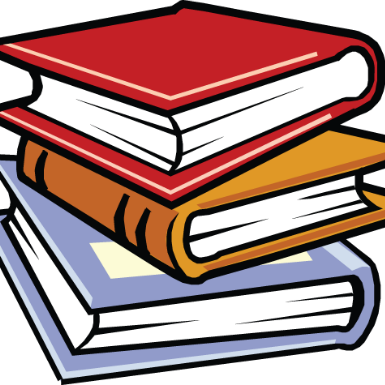2002年6月
老人的朋友給身在北京的我送來了一包裹的茶。裡面有兩袋干的茶葉,是在安徽省的黃山摘下來的。春末是最好的採茶季節,那一趟飛越太平洋的旅程,我的行李裡面滿是新香清冽的味道。
去華盛頓特區看波拉特的時候,我順便去了一趟弗吉尼亞州的賴斯頓,到了當地的老人院。藍色的地毯,白色的牆,輪椅專用的軌道……這個地方讓人感覺千篇一律而單調,隔著一段距離來觀照晚年,通常都有這種感覺。我沿著靜悄悄的走廊一直走到823房間。房門上貼了張貼紙,上面畫著一面美國國旗,還有一行字:「2001年9月11日」。
我敲了敲門,巫寧坤應聲而來,當我把那兩袋茶葉遞給他時,他高興地笑了起來。「這是以前宮廷所用的茶。」他說:「看看這種綠色——不是很美麼?遲一些它會變成紅色,但現在還新鮮的時候就是這樣子的。」
他說茶是他想念中國的一個地方。除此之外,他對新的美國生活並沒有什麼抱怨。我坐了下來,他倒了兩杯萬事好法國白蘭地(Raynal French Brandy)。
巫寧坤喜歡把自己形容成一個「發戰爭財的人」。1937年,日本入侵了他的家鄉江蘇省,在江蘇省的省會城市,日本人犯下了「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巫寧坤當年17歲,他向中國西部逃亡。他的童年並不快樂:他媽媽在他7歲的時候自殺了,而逃亡的生活讓這個年輕人有了一個新的開始。在四川省念完高中以後,他在昆明上了大學,學習英語。他給美國「飛虎隊」的志願飛行員做翻譯,這些飛行員在四川的基地與日本人開戰。中日戰爭以後,巫寧昆獲得了曼徹斯特學院的獎學金,這個學院位於美國的印第安那州,巫寧昆成了學校裡唯一一名外國學生。1948年,他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的博士學位。這些就是巫寧昆的「戰爭財」了——全是學術上的。
1949年後,如同很多身在美國的中國年輕人一樣,巫寧昆面對著一個困難的抉擇。好些芝加哥大學的畢業生回到了新中國,包括趙露西(趙蘿蕤)。身在北京的她敦促巫寧昆回國從教,最後巫寧坤同意了。他的博士論文「T.S.艾略特的重要傳統」還未完成。他研究生院的其中一個朋友,一個叫李政道的物理學者來到了三藩市,送他離開。巫寧昆問他的朋友為什麼決定留在美國。李政道說:「我不願意被人洗腦。」
故事就這樣繼續。1955年,巫寧坤被稱為「反革命」;1957年,他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他被送到勞改營裡。隨後的20年,他大部分時間都呆在監獄,或是下放在農村。他有好多回都幾乎餓死了。然而他活了下來,他的妻子李怡愷也活了下來。李怡愷在無數的運動和懲罰當中,都沒有改變她的天主教信仰。
1990年,曼徹斯特學院給予巫寧坤人文文學榮譽博士。巫寧坤獲邀留在學校,用英文寫了一部回憶錄。回憶錄的名字叫《一滴淚》,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這部書出版以後,巫寧坤在北京的工作單位撤銷了他的養老金和住房。他和妻子決定留在美國,那時候他們的三個孩子都已經在國外讀完書,並在美國安頓了下來。1996年,巫寧坤和李怡愷入籍,成了美國公民。
時不時地,巫寧坤會為「美國之音」寫一些報道(「他們付我的酒錢」)。在一篇廣播稿裡,他評論了我寫的第一本書,隨後他給我寄了一份打印的評論稿複印件。那次偶然的接觸帶我走向了過去:巫寧坤告訴我,他在研究生院和趙露西及陳夢家是朋友,隨後我逐漸下了決心,要去追尋甲骨文學者陳夢家的故事。
巫寧坤今年82歲,一頭濃密的白髮,當他說起過去的時候,常常會自我解嘲地哈哈大笑起來。那些年來經受的殘酷迫害,似乎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陰影。他喜歡說另一個關於李政道的故事,那個年輕的物理學者由於不想被洗腦,所以決定留在美國。1957年,巫寧坤被打為「右派分子」的時候,李政道成了諾貝爾獎歷史上第二年輕的獲得者。
「讓我們為陳夢家乾杯,為我的大姐——趙露西乾杯。」巫寧坤說。大姐是一個常用的中文詞彙,用於形容一個感情親密的女性朋友。我們舉杯,然後巫寧坤站了起來,走到他的書桌旁邊。他遞給我兩封信。「這些信是很私人的。」他說。
兩封信都是露西在1990年代早期手寫的。有一封信提到了巫寧坤的書,還提到了那個古老的四合院——我是看著它被拆毀的。她在信裡寫道:
你的書出版了,我現在仍然很興奮……你和怡愷來北京的話,可以住在我這兒。現在我在四合院的西翼有了一間客人房,裡面傢俱都齊全了。你們可以在我這兒吃飯。
「我總是很同情她。」巫寧坤說。「我覺得趙老先生對她不是很好。據露西說,她爸爸本來想把他們家的房子留給她,但那時候她和陳夢家在一起,於是她就把房子給了她的弟弟。後來陳夢家自殺了,她的家沒有了,於是她只好搬回去和她弟弟及弟媳一起住。她弟弟和弟媳佔了四合院裡最好的房間,只給她一小塊地方。他們對她不是很好,三個人甚至都不同桌吃飯的。一個剛剛經歷了文革、又失去了丈夫的姐姐——他們應該多關心她的!她只有兩個小小的房間而已。」
他繼續說道:「露西和他們的性格完全不同。趙老先生和他妻子喜歡打麻將。他還喜歡和萬里及其他大人物打網球。他並不特別在乎教英語的事。他們忙著打麻將的時候,露西正在翻譯惠特曼的作品!」
我們又喝了一口白蘭地。他小小的房間裡擺滿了兩種文明的裝飾品,書架上的書在兩種語言之間變換:Joseph Brodsky(約瑟夫﹒布羅茨基),張紫葛,Vladimir Nabokov(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徐志摩,John Keats(約翰﹒濟慈)。一面牆上掛著李怡愷和天主教教皇的照片,旁邊是一幅合照,裡面有這對夫婦和三個子女、以及子女各自的家庭。巫寧坤和李怡愷的其中兩個孩子和美國人結的婚。(「他們是混血兒。」巫寧坤指著孫子孫女的照片說。)另一面牆上掛著一幅詩人王曾祺寫的毛筆字:
往事回思如細雨
舊書重讀似春潮
我問巫寧坤,他什麼時候聽到陳夢家去世的消息的。
「在文革結束之前。」他說。「我在安徽的時候從小道消息裡聽說的。自殺的不只他一個。我不會這麼做。他們要殺我很容易,共產黨人手裡掌握了所有的生殺大權。他們想什麼時候殺我就什麼時候殺,但我自己是不會自殺的。我媽媽是自殺死的,我不會再那麼做。」
他說在那些政治鬥爭終於結束以後,他直到1980年才見到了露西。
「我們沒有提到夢家的名字。」巫寧坤輕輕地說。「對我來說,如果要我說我對所發生的事情感到抱歉——那是很難出口的。我知道那些話一點兒意義都沒有。我很高興露西沒有提到那些事。她也沒有哭。她意志很堅強。」
文化大革命以後,趙露西患了精神分裂症。後來她的病情好了很多,可以教書和寫作了,1990年代,她翻譯了沃特﹒惠特曼的《草葉集》,這是《草葉集》首個完整的中文版。1990年,她回到了母校芝加哥大學做演講,演講的內容就是她的翻譯。第二年,學校給予她傑出成就獎。她在1998年去世,就在我搬到北京的前一年。
我對這個女人的瞭解都是道聽途說的。有些材料很殘忍——在夢熊的回憶裡,她坐在四合院中,讓紅衛兵剃了陰陽頭。巫寧坤說她拒絕談論過去,但有那麼一些時候,表面的堅強也會崩塌。埃莉諾﹒佩爾斯坦是芝加哥美術館的館長,在露西1990年來訪美國時,他曾經陪同露西參觀美術館。佩爾斯坦說,露西那時候是個迷人而開朗的老太太,但當他們參觀到露西丈夫1940年代研究的商朝青銅器時,露西就完全變了一副模樣。她一看見那些文物,就變得十分激動,以至說不出話來。她說她那本夢家寫的書——《美帝國主義掠奪的我國殷商銅器》,已經在「文革」中被奪走了。
在我開始進行調查的時候,我就知道要找出陳夢家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現在為時已晚。他的故事隨著一場場過去的政治運動消失,而他屬於失落的一代:那些受過教育的精英分子在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中苦苦掙扎。今天的中國是一個關於未來的故事,它的發展由新生的中產階級推動;實用主義取代了以前的理想主義。如今要緊的是新興的城鎮和大批的移民——像艾米莉和威廉﹒傑佛遜﹒福斯特這樣的年輕人,在這個日新月異的國家中尋找著自己的發展道路。作為一個記者,年輕也很有幫助。這份工作需要活力和自由;你必須跟得上每個人急匆匆的腳步。我是輕裝上路:沒有家庭,沒有永久的居所,沒有辦公室。我的辦事處就裝在袋子裡——一個圖章和一些簡單的執照。
但追查陳夢家的故事越久,在過去的回憶中搜尋越久,我就越欣賞那些倖存下來的人們。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們要逃離戰爭、饑荒和政治,他們嘗試著調和西方思想和中國傳統。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失敗了,但他們並沒有喪失自己的尊嚴,而他們的一點理想主義火花則以某種方式倖存了下來。我在艾米莉和威利這樣的年輕人身上看到了這種理想主義,儘管身處這個實用主義壓倒一切的時代,他們仍然在乎正義和非正義之分。
而上一代人的人已經以某種方式獲得了自身的安定。無論如何,他們都得到了憩息,從他們身上感到了一種平靜。每次採訪完一位老人以後,我返回到日常的世界——一座座一夜之城,一個個爆炸性的新聞,都擁有了一種新的視野。所有這一切都會隨著時間消逝。
每位長者都有自己的方式來處理回憶。石教授在台灣耐心地工作,研究著他以前在安陽所做的考古記錄。王軍用馬尼拉紙做的文件袋收集一個老婦人的謊言;夢熊則加入了共產黨。李學勤攀登上了學術生涯的巔峰,但他並不曾讓驕傲沖昏了頭腦,以至於能毫無愧色地面對年輕時寫下的對陳夢家的批評稿。而趙老先生——有時,當別人控訴他不尊重他的姐姐、也不尊重他已故的姐夫時,我就會想,也許四合院的拆毀是冥冥之中對他的某種報復。
但每個故事都有種種的見解,在北京,我也和陳夢家以前的一個學生王世民見了面。趙老先生和上海博物館為陳夢家的明朝傢俱談判時,他曾充當兩者的中間人。王世民說,沒人有資格責怪趙老先生因為那批傢俱而接受了博物館的錢。「他有權這樣做。」王世民告訴我。「坦白說,其他人不應該為此說三道四。」我明白他的觀點:與其試圖找出誰做錯了什麼,不如去理解政治運動如何破壞了生活、友誼和家庭——這些要重要得多。我也理解趙老先生為什麼寧願打網球,而非沉浸在那些可怕的回憶裡。對於那一代人來說都是這樣——我從來沒見過一個倖存者有其他的反應。過去那些歷史性的事件令人難以想像,它們似乎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事情;而人們對此的反應完全是能讓人理解的。從過去中復原,儘管存在著各種方式,都是人的直覺而已。
但我特別敬重巫寧坤對此的平靜。他的回憶錄並不是暢銷書,但他理順了他的過去。對於任何作者而言,那就是寫作的根本動機,特別是對那些遭遇了不幸的人們。寫作可以模糊真相、困住在生的人,它可以具有破壞性,也可以具有創造性。但對意義的搜尋,則有了一種超越一切瑕疵的尊嚴。
在我們的談話中,老人提到,他對他的人生沒有遺憾。「如果他們沒有搞文化大革命和反右運動,我可能會成為一個更出色的學者。」他說:「我可能會寫出幾本關於英國文學或美國文學的書。但那又如何呢?這些書已經很多了。《一滴淚》這種回憶錄也許更重要呢。」
李怡愷回來的時候,我們還在喝白蘭地。她剛參加完當地的一個天主教集會——16執事的任命儀式,脖子上戴了一個金色的十字架。她聽到她的丈夫正在談論過去的事,就搖了搖頭。
「可能是年齡的關係吧,我特別的健忘。」她說:「我老忘記把東西放在哪裡了,也記不住新的事情。但所有過去的事情我卻記得很清楚。有時候我甚至還記得很多的細節,記得發生的日期和時間。我的女兒說,你怎麼能記住那麼多細節的呢?」
巫寧坤笑了起來,抿了幾口白蘭地。
「例如我丈夫被逮捕的日子。」她說。「那是1958年4月17日下午兩點。我總是記得那個時間。我也記得我三次去河北監獄看他的事情。」
我問巫寧坤,他在監獄和勞改營的那些年,是怎麼讓自己保持積極的心態的。
「那時候我會想起杜甫、莎士比亞和迪蘭·托馬斯。」他說。「你知道迪蘭·托馬斯在父親臨終前寫下的那首詩歌嗎?《而死亡也不得稱霸》裡頭有一句『在刑架輾轉精疲力竭』。(註:此處採用的是北島的譯本)這和我們的行為相關——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儘管我們遭遇不幸,儘管我們在忍受折磨,但『死亡也不得稱霸』。你知道嗎,我在芝加哥聽過迪蘭·托馬斯朗誦他自己的詩歌。我記得是在1950年。他的朗誦非常令人感動。」
我問巫寧坤,他有沒有和這個威爾士詩人說話。
「沒有,我只是聽眾而已。」他說。「而且那時他已經醉醺醺的了。他不懂得如何照顧自己。他在受苦——我覺得,人生成了他的一個負擔。」
輪椅專用的軌道,白色的牆,藍色的地毯。我站在養老院外面,在午後的陽光中瞇了瞇眼。在我面前,是一連串經典的美國零售店:漢堡王(Burger King)、西夫韋(Safeway)、好萊塢影像(Hollywood Video)、裡朵皮薩(Lido Pizza)、辛辛那提餐廳(Cincinnati Cafe)。我走到一間便利商店裡,買了一杯飲料,然後回到養老院門前的長凳上。公交車幾分鐘後應該會來了。三個老婦人坐在我旁邊的長凳上。看樣子她們就等著和人聊天了。
「好喝嗎?」其中一個老婦人問道。我點點頭,放下手裡的飲料。
「小心身材走樣喔。」另一個老婦人乾巴巴地說。她有很重的紐約口音。
「你來這兒看誰呀?」第三個老婦人問。
「巫寧坤。」我答道。「巫寧坤和他的太太。你們認識他們夫婦嗎?」
「當然!」
「每個人都認識巫先生!」
我問她們為什麼,結果三個老婦人一起瞪著我,好像我是個傻瓜一樣。
「因為他的書啊,還有因為他上過芝加哥大學。」其中一個平靜地說。她的話聽起來耳熟,是中西部那種平平的口音。我問他們有沒有讀過《一滴淚》,話出口就意識到自己又問了個蠢問題。在弗吉尼亞州萊斯頓的這個角落,巫寧坤簡直就是家鄉人引以為傲的作者。
我問她們對那本回憶錄有什麼看法。
「我喜歡那本書。」一個說。
「他有一段艱難的人生。」中西部口音的說。
「尤其是他被發配到勞改營的日子,很艱難。」紐約口音的說。
公交車開到了跟前,車門打開了,滋滋作響。一幅景象忽然清晰起來:三個年老的姊妹,在紡紗、織布、剪掉線頭。我停住了,不知道要怎麼結束我們的談話。
「你快點上車吧。」紐約口音的說。我就照辦了。
在北京大學的圖書館的圖書館裡,朋友幫我找到了兩冊《草葉集》的中文版。它是在1991年出版的,封面的顯著位置標明了譯者是趙露西。
1994年,一位研究惠特曼的美國學者肯尼思·M·普裡斯,來到北京拜訪了露西。他們的談話發表在《沃特·惠特曼季刊》裡。在訪問中,普裡斯問露西,她怎麼翻譯詩歌《跨出永不止息的搖籃》(Out of the Cradle Endless Rocking)的第一節,那一節前22行是一個很長的句子,而主語和謂語動詞在22行之後才出現。
露西回答:「沒有辦法把那個長句翻譯成一個句子。我必須要說,雖然我想盡量忠實原文,但我也要考慮中文譯文的流暢性。」
我重新讀了一遍惠特曼的原詩,然後看了露西翻譯的中文版。我用字典查了一些較為艱澀的字眼,然後盡我所能把她翻譯的詩歌第一節的最後三行重譯回英文:
我,痛苦和歡樂的歌手,今世和來生的統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來,加以利用,但又飛快地躍過了這些,
歌唱一件往事。
I, 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
the uniter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ving all silent signs, using them all,
but then leaping across them as full speed,
Sing of the past.
一個甲骨文學者曾經說過:那些是音符。我們必須自己譜出歌曲。
(全書完)
附:惠特曼原詩Out of the Cradle Endless Rocking第一節最後三行:
I, chanter of pains and joys, uniter of here and hereafter,
Taking all hints to use them, but swiftly leaping beyond them,
A reminiscence 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