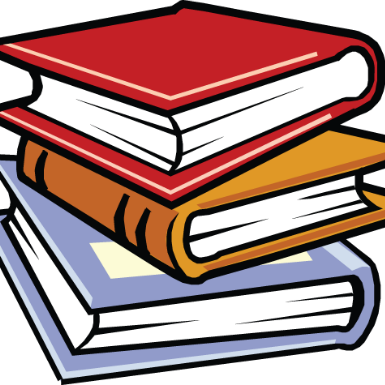2002年1月
波拉特的第二任房東是個美籍華人。那男人在廣東長大,「文革」時期,他的父親坐著小船逃到了香港。最後,他父親獲得了美國的政治避難身份,並把他的幾個兒子接了過去。有一段時間,他的一個兒子在華盛頓特區開了家中餐館。後來他把餐館賣了,在第六大街西南投資,買了兩排紅磚房。房東和他的家人住在其中一間房子裡,其他的部分就租給移民住。
波拉特租了這個中國家庭樓上的一個房間,一個月的房租是260美元。他的住所呈正方形,長寬都是9英尺;牆上什麼裝飾也沒有。房間裡有一台彩電,一個電爐,一個煮水器,一台電暖器。還有五本書,全都是學英語的資料。桌子上放了一個中式的手撕檯曆,日期停留在某一個隨意的日子上:2001年10月14日。房間裡只有一扇窗,窗戶就在兩條細細的輸電線之間。
這房間很小,波拉特也不願意和一個中國家庭共用洗手間。他們極少交談——事實上,波拉特和房東甚至沒有交流過彼此的移民經歷。波拉特避免和中國人討論他的政治背景,而房東也沒有興趣分享他自己的故事。房東的事情是波拉特從別的租客口中聽說的。
這樣的關係很奇怪,但這地方的位置,比起富蘭克林和羅得島大街交界的那個角落(註:波拉特剛到美國住的地方)可好得多了。在華盛頓特區網狀分佈的街道上,波拉特移向了中心:他如今住的房子就在第六街和Q街交界的附近。過去,這一帶被稱為肖姓區或芒特弗農區,但如今它逐漸變成了唐人街的一部分。 這個地方在不斷變化,新的華盛頓會議中心就建在附近,而且政府準備把當地的一些補貼住房改造為市場上的出租房。以前這一帶住的基本上是黑人和窮人,但如今來了不少新的居民。許多移民搬進了這個地區,其中大部分是中國人,還有有些年輕的、屬於中產階級的白人。離波拉特家幾個路口之遙,一個同性戀團體建立了大都會社區教會。
種種早期跡象顯示,這兒似乎要由破敗社區改造成良好的中產階級居住區;可能第六街最後會延續這種繁榮的多樣化,這種多樣化在美國城市的社區裡是很少見的。但如今,從波拉特的住所往南走,仍然可以看見黑人區和中國人區的舊分界。第六街沒什麼商業建築,許多的連排式住宅都是破破爛爛的樣子。保存得最好的地方是一些傳統的黑人教堂:斯普林菲爾德浸信會、上升錫安山第一浸信會、加爾佈雷思非洲衛理公會主教派錫安教會。在L街的轉角,是厄立特裡亞文化娛樂中心;而在隨後的I街,一座磚樓的牆上漆著一個舊標識:福建居民協會。
再往南走,就到了小小的唐人街的中心地帶。沿街是一溜的餐館和店舖:中國男孩熟食店、唐人街市場等等;幾乎所有地方都懸掛著美國國旗,這在黑人居住區是很罕見的。在H街,沿街的美國國旗掛得密密麻麻,一路都是雙語的標誌:China Doll Restaurant(麗華園)、Eat Fisrt Restaurant(食為先)、Wok N Roll Restaurant(珍味樓)。在H街和第七街交界附近,豎立了一座中國式的牌樓,作為入口的大門。牌樓上的刻字標明,這棟建築是1986年時由北京市長陳希同和華盛頓市長馬裡恩·巴裡共同出資所建,是一座「友誼牌樓」。這座牌樓卻產生了意料之外的巧合:在「獻給友誼」的牌樓建起後幾年,兩個市長都進了監獄。1990年,巴裡因藏有強效純可卡因而定罪;8年以後,北京的一家法院宣佈陳希同犯了貪污罪。但這一條特別的中美關係並沒有在牌樓上註明,在美國首都整齊的網狀街道下,這是又一條潛伏的岔道。
唐人街的標誌在兩個世界中轉換,這種轉換也並不均等。英文名字裡那種玩笑似的種族主義,翻譯成中文後就消失不見了:中國甜姐兒餐館(the China Doll Restaurant)變成了美麗的中國花園——麗華園;而中國男孩熟食店(China Boy Delicatessen)則通過「中國孩子的新鮮麵條」這個名字獲得了某種尊嚴(當然還有一條完全不同的產品線)。炒鍋和面卷餐館(the Wok N Roll restaurant)把自己改造成了珍貴滋味的餐廳——珍味廳。在H街和第八街交界,豎著一個「唐人街禮品」的英文廣告標誌,但中文標誌的意思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上面寫的是: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我覺得,這跟我在北京去的那家地方一樣,就是些做假簽證生意的公司。」有天晚上,當我們開車經過唐人街的這個標誌時,波拉特說道。「那種公司必須要在美國有聯繫人,我想那家所謂禮品店就是幹這個的。他們會安排好各種信件,就像我從洛杉磯帶來的那些信一樣。那標誌上的『國』指的是『中國』。誰離開美國會需要幫助呢?」
1月裡一個寒冷的下午,我陪著波拉特去上班。上一年10月份的時候,他找到了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給市中心一家叫「亞洲餐廳」的小餐館送外賣。他已經有一些維吾爾族朋友在那兒工作了,對於一個不太會說英語的移民來說,這是一份相對容易的工作。送外賣是在晚上,這樣波拉特白天就有時間學英語了。他最近剛上完兩個月的課程,如今能懂得相當一部分的英語詞彙了 ——他開車時常常聽電台的新聞。不過他說英語還是不習慣,如果可能的話,他還是願意用中文。
但他的車技已經很精湛,一看就知道他屬於「上班族移民」。他諳熟華盛頓那些縱橫交錯的街道:單行的道路,交通高峰期塞車的路段。他還知道如何緊貼著路邊違法超車,或者假裝無心地衝過停止標誌。他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掉頭。他總是留意著警察;在送外賣的時候,他還是能立即找出停車位的老手。如果沒有停車位,他隨時能就地湊合:停車,打開危險信號燈,然後匆忙而去,暗自希望不會吃罰單。他開車的時候,總是用英語說著一個單詞;他一遍遍地重複著,就像在禱告:「停車,停車,停車。」自從工作以來,他已經付了600多美元的罰款了。到目前為止,他一天最多的紀錄是三張罰單:兩張20塊美元的違規停車罰單,一張50塊錢的,是懲罰他在交通燈黃色轉紅色的時候沒有停車。在亞洲餐店,他的酬勞是7美元一小時,另外再加上小費。
他出過一次車禍。上一年12月的時候,他出去送外賣,在賓夕法尼亞大道的紅燈路口前停下,後面有輛車撞了上來。那輛車的司機開得太快了。他們兩人分別從車裡下來以後,波拉特聞到那人的呼吸裡有酒味。那人把波拉特本田車的後保險槓整個撞了下來。
「他開始和我說話的時候顯得很友善,但他一發現我是外國人,英語說得很糟糕,他就開始恐嚇我了。他對我說,不要叫警察,會惹上很多麻煩的。他說我可以去把車修好,他出一半的錢。我同意了。不過我現在知道我應該要叫警察的。當時我想著,如果警察來了,我還要叫一個會講英語的朋友過來,太麻煩那個朋友了。後來,我所有的朋友都說我應該叫警察。我有買保險,有汽車執照,而且沒有違反任何的法律。我的朋友的都說,我不應該相信任何一個非洲人。」
換一個新的保險槓要1000美元,開始那個司機說給波拉特500。但波拉特從來沒有收到他的支票;波拉特去他的辦公室找他,那人就把價錢降到了300美元。波拉特不情願地答應了,然後就是等待——還是什麼也沒收到。後來那人把錢降到了100美元,波拉特就威脅他說要請律師來解決。最後,那個人給了波拉特150美元。波拉特找了個中國的汽車修理工,用低價幫他把車修好了,花了300美元。
波拉特還留著那個司機的名片,上面寫的地址在十三街西北面。
「我覺得那人在做一些騙人的生意。」波拉特對我說。「那個地址上只有一個普通的房子,裡面有一張桌子和一個電話。他甚至沒有電腦、沒有打印機,沒有所有這些基礎設備。我想他的生意應該和建築業有關。」
不過,波拉特並不想從那人身上拿回更多的錢了。他開車開得棒極了,但只要一踏出車門,這種流暢就蕩然無存。而且他知道自己的駕駛記錄並不完美。除了那些罰單以外,總存在這麼一種可能:有人仔細察看了他弗吉尼亞州的駕駛執照,意識到這執照是用一份偽造的宣誓書獲得的。在9.11恐怖襲擊事件過去10天以後,這個法律上的漏洞就被堵住了,因為19個劫機犯中有7個登機時用的身份證明,都是從弗吉尼亞州非法獲取的。
亞洲餐廳前面的招牌寫著「異國佳餚」。菜單上大部分是日本菜,但上面也有來自東方各個國家的菜式:新加坡炒麵、泰式料理、檳城蝦麵湯、左宗棠雞。廚房裡的廚師有泰國人、印度尼西亞人和南美洲人。墨西哥人負責洗碗。我們第一天出去送外賣的時候,做壽司的師傅是馬拉西亞人和廣東人。這些師傅穿著日式的寬鬆外衣,對著靠街的窗戶,在明亮的燈光下工作。從我們站的地方看過去,裡面很暖和。
那一晚上,給亞洲餐廳送外賣的全是維吾爾族人。溫度只有華氏20度左右(註:攝氏零下6.6度),我們四個人縮成一團,等著客人下單。和波拉特一樣,另外兩個維吾爾族人也是最近才來美國的。一個的足跡從新疆到哈薩克斯坦到烏茲別克斯坦;另一個在土耳其長大,他的家人以難民的身份在那兒定居。
「我來這兒的原因是因為我不想去軍隊服役。」他解釋道。「在土耳其,每個男人都要服兵役。生活可不是那麼容易。」
那個維吾爾族人輕輕地說,在寒冷中裂開嘴笑了。他是個高大而英俊的男人,有一頭短短的黑髮。我問他年齡是多少。
「23年老。」(Twenty-three old years.)
他的語法錯誤是無心犯的,但我喜歡這個句子的微妙轉折:一個年輕移民的老年頭。我問他
土耳其公民需要服多久的兵役。
「兩年老。」他說。
「服兵役有危險嗎?」
「以前比現在更危險,因為北部有恐怖分子。但現在情況沒那麼糟了。我不想去的主要原因是服兵役太無聊了。」
波拉特給大家派發了他的萬寶路煙,這些維吾爾族人背著風,把煙點著了。餐廳裡面一派忙碌的模樣,大部分的顧客都是剛剛下班的年輕白領。情侶們匆匆走過寒冷的街頭,從我們這一群吸煙的維吾爾族人身邊經過。旁邊是另一家的亞洲餐館「泰國之星」,再過去是「阿曼德芝加哥比薩店」。每個地方門口都掛著美國國旗:自從恐怖襲擊以來,似乎每個做生意的人都需要有至少一面這樣的旗子。
波拉特打電話叫了一個維吾爾族朋友,他就在附近的自由亞洲電台工作。那人來了,加入了我們的隊伍。他的名字叫阿林·賽托夫,他告訴我,他是唯一一個擁有美國新聞學位的維吾爾族人。他曾在查塔努加市的田納西大學學習廣播新聞學(在那以前,他在田納西讀過基督復臨學院)。他今年32歲,是個瘦高個兒,穿著黑色的皮夾克,一副嚴肅的模樣。他痛心地說起了國際社會對新疆情況的無知。
「在中國,我們比其他所有的少數民族都有更多的麻煩。」他說。「比西藏人的麻煩多多了。但西藏人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因為他們有達賴喇嘛。我的爸爸是政治犯,在監獄裡呆了十年。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我已經11歲了。我爸爸認識一些被處決的人。」
一個白種女人從亞洲餐廳裡走出來,手裡拿著外賣的盒子。她剛好聽到阿林說的最後幾個字,突然回了一下頭。她琢磨了一下這群縮成一團的維吾爾族人,然後繼續往街那頭走,腳步更快了。阿林似乎沒有留意。「幾乎每個維吾爾族的家庭裡,都有人曾經在監獄裡呆過一段時間。」他說。「他們竟然仍舊保持沉默,這讓我很驚訝。」
另一個維吾爾族人送完一次外賣回來了。他20多歲,長著一個高鼻子,頭上戴一頂嘻哈潮牌棒球帽。波拉特離開去給他的本田車加油時,「嘻哈潮牌」會意地笑笑說:「停車。」這是我聽到他說的唯一一個英文詞彙。波拉特告訴我,這個人5個月前從加拿大偷渡來美,他的家鄉是新疆一個邊遠的地方,他甚至連中文也不會說。
過了一會兒,大家決定是時候吃晚飯了。他們可以在亞洲餐廳免費用餐,但大家都寧願到別的地方去。(「我一年吃一回日本菜就足夠了。」波拉特說。)我們去了旁邊的阿曼德芝加哥比薩店,裡面的夥計都是摩洛哥人。由於伊斯蘭教移民之間的淵源,他們熱情地招呼這些維吾爾族人,還給我們買比薩餅打折扣。比薩餅裡沒有豬肉,和芝加哥一樣。我問阿林他對阿富汗戰爭怎麼看。
「我覺得非常好。」他說。「我比美國人更討厭塔利班。如果他們不把塔利班幹掉,大家也許會把那些人和維吾爾族人聯繫起來。這就是中國人希望發生的事。他們搭上了這場針對恐怖主義戰爭的順風車。中國人回應總是很慢;起初發生恐怖襲擊的時候,我覺得他們並不知道該怎麼做。後來他們就想,為什麼不利用這個機會呢?」
中國其中一個策略就是給舊的問題起了個新名字。9.11恐怖襲擊以後,中國的官員和國家掌控的媒體開始提到在阿富汗和其他中亞國家受訓的「東突恐怖分子」。過去,他們通常把維吾爾族的異見分子叫做「新疆分離主義者」。這個新名詞聽起來更加像外來詞,這樣的稱呼似乎打算要讓美國人對中國人更為同情:他們一邊被外部的伊斯蘭恐怖主義者威脅,一邊要被迫要應付國內的一支不滿現狀的少數民族。2001年11月,中國外交部長向聯合國報告恐怖主義的情況時,他特別強調中國的「東突恐怖分子」問題。
中國要求把維吾爾族的群體列為打擊恐怖分子戰爭中的敵對名單。但美國國內有反對之聲。一些維吾爾族人的忠實同盟者是保守黨人。2001年10月,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在《華盛頓時報》的專欄版發表了一篇評論:
如果美國最後從北京方面得到反恐方面的支持,幾乎可以肯定,美國將以默許中國鎮壓維吾爾族人作為代價(再加上中方鎮壓西藏和孤立台灣的嘗試)。
這將成為一場道德上的大災難,把維吾爾族人和那些窮凶極惡、已經對我們造成危害的狂熱分子混為一談,毫無公正可言。維吾爾族人在北京當局的暴政之下合理地爭取自由,他們的抗爭大部分是和平的行為……
參議員赫爾姆斯也是自由亞洲電台維吾爾語廣播的主要支持者。這個電台和美國之音相似,但出現的時間要晚得多;它在1996年開始廣播,播音語言有亞洲各國不同的語言,其中包括了普通話。1998年,增加了維吾爾語的廣播服務。每天,它會播出兩個小時的新聞和其他節目,新疆和中國其他部分的短波電台都能收到。對自由亞洲電台的資助,有時則成了美國勉強接受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砝碼。2000年5月,眾議院通過了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的提案,同時附上一個條款:增加對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的資助。這安撫了國會裡一些反對中國的情緒:美國人接受中國經濟力量強大的事實,但他們通過支持獨立的廣播電台,表達了對其政治制度的鄙視。
問題就是,實際上美國國內沒有任何人瞭解,通過電波發送出去的到底是什麼。(譯者註: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是由美國政府資助的,為避免政府進行灌輸性宣傳和左右公眾輿論,美國法律規定美國政府傳播給國際受眾的消息,不能在美國國內傳播。)一個進行中亞研究的學者告訴我,自由亞洲電台的維吾爾語廣播節目比普通話、藏語的廣播要激進得多,他擔心這種資訊服務只會帶來激怒中國政府的後果。他也擔心,維吾爾族人高估了像赫爾姆斯這種領導人對他們的支持。在中亞,這是老生常談的事情了:美國的一個慣用策略,就是鼓勵少數民族或宗教群體對抗更為強大的力量——例如蘇聯或中國。一旦這種地緣政治有所轉移,來自美國的支持就結束了,反抗的群體也隨之被人遺忘。這種「鼓勵——忽略」的美國模式,助長了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
這就是寂寂無名的代價:像維吾爾族這樣地處偏僻的小族群,幾乎沒人能從他們本身的角度出發去理解他們。中國人把他們看成是共和國裡的一支少數民族;土耳其語系的族群把他們看成突厥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把他們看成伊斯蘭信徒;參議員赫爾姆斯把他們當作反對中國和支持美國的力量。他們就像是那些新疆出土的木乃伊一樣:關於他們的信息少之又少,以至任何人都可以在自身的想像中重構這一個小民族。而又有那麼多對當局不滿的維吾爾族人,隨時準備轉向任何外來的支持。
在華盛頓特區,我和梅赫梅特·歐麥·卡納特見了面,他是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報道了最近的反恐戰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卡納特採訪了6個維吾爾族的囚犯,他們是與塔利班並肩作戰以後被捉住的。據卡納特估計,在某段時期,到阿富汗受訓的維吾爾族人有幾百個之多。他採訪的6個囚犯都是年輕的男人,年齡在20歲到30歲出頭,他們來自維吾爾族傳統社會的各個階層,有農民、商人和知識分子。有個囚犯曾在一所中國的大學拿到經濟學的學位。他們最後都會被送往位於關塔那摩灣的美國審訊中心。
「他們不想別人把他們當作恐怖分子。」卡納特告訴我說。「他們說,他們和阿拉伯人以及基地組織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們和塔拉班一起作戰,只是因為戰爭爆發時他們正在那兒受訓。他們說,這是一場內戰,我們並不想牽涉其中。我們想要和中國開戰。我們來到這兒,只是想利用這個機會。」
我問卡納特,他們對美國的態度如何。
「他們並不生美國的氣;他們很高興。」卡納特說。「他們告訴我,可能美國會在阿富汗建立一些基地,那麼美國就將成為中國的鄰居了。他們滿懷期待。他們希望美國人會幫助他們對抗中國。」
晚上7點30分過後,亞洲餐廳的外賣訂單增加了。波拉特接到的第一個訂單地址在K街的1900號,那是一座辦公樓,前面的標誌牌上列出了一些律師事務所,還有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一個分部。波拉特把警告燈打開,在K街上違章停車。接過外賣的金髮女人右手殘缺不全。她給了兩塊多美元的小費。
「每次從她那兒拿小費,我都覺得很不好。」我們走回去停車的地方時,波拉特說道。「她總是非常友善。還是個殘疾人。」
「我就不會為這個煩惱。」我說。「她應該是個律師。很可能賺很多的錢呢。」
「我知道。」他說。「但我仍然覺得很不好。」
第二份外賣訂單把我們帶到了L街。波拉特在十三街轉了個彎,看了看倒後鏡。
「我將要違反一條美國的法律了。」他宣佈道。「這兒有雙橙色線。如果警察看到了,他會罰我30美元。」
他很快地掉了頭,在荷馬大樓前違章停車。沒有警察。更多的律師事務所出現了:12層樓高的中庭掛著一幅巨大的美國國旗,還擺放著一座青銅雕像,雕像的名字叫做「美國青年之精神」。上面的刻字顯示,這座雕像最初是為奧馬哈海灘紀念館所設計的,那座紀念館位於法國的諾曼底。當我們走進大樓時,警衛朝我們笑了笑。
「這個警衛人很好。」我們等著顧客取外賣時,波拉特說。「我常常到這兒來。他總是對每個人都很友善。」
這個中年警衛和一個年輕一些的男人在聊天。這兩個黑人說話時旁若無人,似乎我們並不站在他們旁邊;很多美國人聽到我們用別的語言交談時,說起話來都會這樣。在荷馬大樓裡,那年輕一些的男人談起了一個女人,警衛在給他一些建議。
「你這麼做很酷。」年長一些的警衛說。
「我這麼做很酷。」年輕男人表示同意。
「你這麼做很酷。」年長一些的警衛又說了一遍,臉上掛著心照不宣的微笑。
這個夜晚逐漸忙碌了起來,每次我們回到亞洲餐廳,總是已經有另一份外賣訂單在等著我們。加州壽司卷、牛肉拉麵和天婦羅蝦卷外送給妮可.厄爾布。左宗棠雞和涼拌海帶外送給蘇菲·可助(Sophie Kojuch)(波拉特說,這名字看起來像土耳其語。)到了客人住的大樓,波拉特一般都在樓下按了對講機,說話只用兩個英文單詞:「你好,外賣。」很多客人都是晚上加班的律師;他們下了樓,睡眼惺忪的樣子,笨手笨腳地摸索錢包或皮夾。沒有人朝我們倆多看一眼。如果他們要知道所有左宗棠雞背後的故事,還得花上好些時間。這個雞的英文名字把左將軍給拼錯了,把General Tso拼成了General Tao;左宗棠是清朝一位聰明絕頂而極其殘忍的將軍,是他拓展了中華帝國的疆域。在左宗棠的統率下,1884年,新疆納入了中國的版圖,成為了中國的一個省份;而現在,維吾爾族人在美國的首都送外賣,外賣的食物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雞。左將軍和山德士上校(註:即KFC老爺爺),他們都是絕妙的「雞肉帝國主義者」。不要吃肯德基,不要吃新疆。
最後一趟外賣把我們帶到了馬薩諸塞大街1701號。波拉特在一塊寫著「任何時候都不准停車」都牌子前面停了車,走進樓房的大廳,經過另一塊「絕對禁止交付外賣」的標誌牌。接過外賣的女人給了波拉特12美元加12美分的小費。到了二十五號大街上,波拉特把車開到了專門給救火車用的防火道上。轉回到十九街,一輛出租車超車時擋住了我們的去路。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白人開出租車。」波拉特說。「都是外國人。他們對城市的交通帶來了很壞的影響。那些出租車司機開車甚至比我還不守規矩。」
波拉特的下班時間是晚上10點。今天是發薪日,在亞洲餐廳裡,墨西哥洗碗工們排著隊來領他們的支票。維吾爾族人拿出他們各自的小費,然後再把總數平均分成五份,每份是26美元。波拉特兩周的薪水是544.38美元。波拉特領了薪水,我們就往外頭走,到街對面打收費的公用電話。波拉特要打電話給他的妻子,他的手機帳單最近高得嚇人,於是他就開始用電話卡打電話了。此時風寒刺骨,一個目露凶光、身穿皮大衣的黑人踉踉蹌蹌地向我們走來。
「你們要不要泰諾?(註:Tylenol,毒品的一種)。他說:「3塊一盒。」
波拉特和我一起盯著他看。
「泰諾!」他大喊了一聲。「3塊一盒!」
「不要,謝謝。」我盡可能禮貌地回答他。那人蹣跚著向街那頭走去,邊走邊憤怒地說著什麼。
「你確定在這個地方打電話安全嗎?」我問他。
「沒事。」波拉特說。他按下了一串號碼——在烏魯木齊的某個地方,一台電話響了,但沒有人接聽。我們開車回到他連排式住宅裡。波拉特讓我在他的房間裡過一宿,他就去隔壁住的維吾爾族朋友那兒睡一晚沙發。我們走進房子裡,波拉特的中國房東正坐在客廳裡。他一看見我,就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這是我跟你說過的那個朋友。」波拉特說。「他是美國人。」
那人觀察著我,眼神裡有些懷疑。「我們是在北京的時候認識的朋友。」我邊說邊露出了微笑。「我住在北京,但我是個美國人。我來這兒看望他。」
「噢,你說中文。」房東說。他臉上也露出了笑容,但他的嘴巴抿緊了——我在中國見過這種神情。他問波拉特能不能私底下和他談談。
我在波拉特小小的房間裡等著。過了一會兒,波拉特回來了。
「房東不讓你在這兒住。」波拉特說。「他說你是『外國人』。」
波拉特用力吐出了「外國人」這幾個字眼。在中國,我已經習慣了當一個「外國人」,但在這兒的唐人街,問題不是在「國」上面,問題是「外人」。外人就是陌生人。
「沒關係。」我說。「我去旅館住也很方便。我不想給你添麻煩。」
「他說你可以住到隔壁我朋友那兒去。他只是不想讓你留在他的家裡面。」
「我明白。他們不認識我。」
波拉特生氣地咒罵起來。他說:「中國人到處都一樣。」
波拉特晚上送外賣,白天則是空閒的。到了白天,我們就坐著他的本田車在城裡逛:他介紹我認識了一些維吾爾族朋友,帶我去了他平時常去閒逛的地方,例如東南面的「農民集市」,很多移民都在那兒買東西。冬天在外頭觀光太冷了,波拉特喜歡去博物館,有天下午我們一起去了史密斯森博物館(註:即聯合國博物館)。展覽的名字叫做「田野到工廠」,介紹是這麼寫的:
美國已經成了成千上萬移民的天堂,這些移民因逃離戰爭、貧窮、歧視或追求自由而來到美國。但是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時期,美國社會卻壓迫自己的人民。
有一個展覽展示了1915年到1940年期間黑人自南而北的大遷徙。其中展示了一個狹小的房間,是供這些臨時過客住宿用的,裡面有一張床,一個床頭幾,一個櫃子。我們靜靜地站在房間前面,不約而同地聯想到了同一件事情。最後,波拉特大笑地說出了我們的想法:「這應該比我的房間要好吧。」
附近是另一個展覽區,標題是「這值得嗎?」下面引用了一封匿名信,這封信收集在社會學家查爾斯.吉翁.約翰遜所著的《芝加哥的黑人》一書中:
我以為芝加哥是個很棒的地方,但卻發現並不是。舅舅告訴我說他住在波特蘭大道,說那是一條很棒的街道;卻發現它就是個大泥潭而已。我肯定是希望能回家的。
波拉特從未說過要回去之類的話:拿了政治避難身份以後,就不可能再回去了。他常常說他來的時機太壞,他真希望自己在9.11恐怖襲擊之前就已經大概安頓好了。不過,到目前為止,他所遇到的公然歧視還不多。9.11過後幾周,有一次,他在馬裡蘭的艾塞克斯到一個加油站加油,那兒有幾個白人卻叫他走開。他其他的一些維吾爾族朋友也遇到了些小問題,名字聽起來像伊斯蘭教徒的人則發現更難找到工作了。但這種不信任感基本都是隱蔽的,只是縈繞在城裡的一種氛圍而已。「美國人不會當面對你說他們不喜歡你。」波拉特說。「這一點不像中國人。如果中國人不喜歡你,你總是一下子就知道了。美國人很聰明,把真實的感受隱藏了起來。」
波拉特最擔心的事情是他的妻子出不來。他的律師已經替他的妻子準備好了簽證所需的資料,但沒人知道多久才會獲得批准;在恐怖襲擊之後,所有的申請流程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律師認為至少要等一年,可能兩年,也可能還要更久。同時,波拉特也越來越難說服他的妻子,告訴她一切都沒問題了。恐怖襲擊過後的10月,波拉特的手機帳單是488.75美元。
在華盛頓特區,我和波拉特的維吾爾族朋友住在附近的連排式住宅裡。這地方擠得滿滿的:3個墨西哥人住在地下室裡,1個維吾爾族人住在1樓,9個中國人住在樓上的房間裡。除了1個人以外,其他所有住客都做食品方面的工作,他們之間沒什麼交流。似乎沒人在意有個「外人」睡在樓下房間的沙發上。
波拉特的維吾爾族朋友48歲,也是拿了政治避難身份的。他正等著妻子和兩個雙胞胎兒子的簽證申請獲批。他們還在土耳其,這男人已經兩年多沒見到妻兒了。他說如果我的文章裡提到了他,他要求隱去姓名。
他房間的牆上掛著不同語言的標牌,有英文的(停止中國對維吾爾族人的迫害),有阿拉伯語的(偉大的真主阿拉),有中文的(萬事如意)。門上則掛著一本日本歌舞伎的日曆,來自這人送外賣的「日本烤肉兄弟」餐館。他曾在西安一所大學唸書,拿到電子工程專業的學位。最近,他的車被人偷了——這一帶將逐漸變成中產階級居住區,但目前還是發展的早期階段,離目標尚遠。
有天早晨,我們三個聊天,這維吾爾族人說,他對美國人看待文化的角度很感興趣。他說這和他在新疆或中國的其他地方的見聞都不一樣。「我在這兒工作,要送外賣到很多人家裡去。」他說。「通常人們不會叫我進家裡去,不過有時有些人會這麼做,我就能看到他們的家裡是怎樣的。他們很多人家裡都掛著中國畫。他們告訴我,很多美國人喜歡中國。」
我問他是否為這個感到困擾。
「不是,」他說:「欣賞另一種文化是好事。可能這體現了美國人的審美鑒賞很廣泛。我在人們家裡還看到過許多非洲的面具。」
我問波拉特怎麼看,他皺起了眉頭。這些年來,他總是把文化說成是非常神聖的事情,他認為文化比經濟、政治更為基本,是最重要的東西。有一次他跟我說,這就是美國黑人的癥結所在:雖然他們生活在一個經濟發達、政治制度自由的國家,但曾經的奴隸制度已經摧毀了他們的語言和文化;這和那些自由來美的移民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看來,黑人總是努力想要從那樣的創傷和損失中復原。
現在他深思著,字斟句酌地說了起來。「那些美國人有他們自己的文化——歐洲文化,那也是很偉大的。」他說。「但我沒看見他們家裡有很多歐洲的東西。為什麼他們那麼喜歡中國呢?我知道中國人說他們有五千年歷史,但這確實是真的嗎?還是他們一遍遍地這麼說而已呢?」
他繼續說道:「我看到那些中國畫,就想起了我工作的日本餐廳。那兒提供的不是真的日本食物;是假的。那兒的廚師也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是穿成日本人模樣的馬拉西亞人和中國人。我沒有看見有日本人在那兒吃過飯。來的全是美國人。」
「嗯,一家真正的日本餐廳可能不會做外賣。」另一個維吾爾族人說。「他們很講究食材的新鮮。我工作的那家餐廳也不是真正的日本餐廳。其實那兒的老闆是個越南人。」
「我覺得這和美國人的自由有關。」波拉特說。「如果你找到一個賺錢的辦法,你就去做。賺錢才是要緊事,這沒什麼不對。但沒有一個日本人會去那兒吃飯。但餐廳裡的廚師穿成日本人的樣子,就讓我感到煩心。這讓我想起了北京那些維吾爾族餐館,裡面的中國人穿成維吾爾族人的模樣。
波拉特生日那天,他請了一天的假。早上,我們開車在城裡轉,辦了一些事,然後去了趟農民集市。波拉特給我指了指他交違章停車罰款單的政府大樓。電台的廣播員提及了《華盛頓郵報》關於驅逐非法移民的報道。這是個寒冷而晴朗的日子;沒幾個人在外頭。波拉特「46年老」了。
辦完事後,我問波拉特能不能去看一下五角大樓。這個月的早些時候,我去看了紐約的世貿中心遺址。生活在中國讓恐怖襲擊成了一件遙遠的事情:我所接觸的只有那些盜版碟,還有人們毫不同情的反應;現在我覺得我應該去親眼看看那些地方了,我們圍著五角大樓開車繞了好幾圈,最後找到了一家citgo加油站停車,那兒可以清晰地看到哥倫比亞公路對面的五角大樓。我們停車時,電台廣播裡傳出了美國國歌。波拉特告訴我,自從恐怖襲擊以來,每天中午廣播國歌成了慣例。
五角大樓被撞壞的一側樓身已經用板圍了起來,腳手架頂上掛著一幅幅美國國旗。頭上有盤旋的巡邏直升機,發出嗡嗡的聲音。三個挪威旅客也找到了這個加油站。我們就站在這三個外國人旁邊。波拉特時不時回頭看一眼他的本田車。
「沒事。」我說。「他們不會在加油站開罰單的。」
「這個加油站可能不一樣。」他說。
我走到加油站裡面,買了一份《華盛頓郵報》。上面的頭版頭條是:
美國搜尋數千個被驅逐出境的在逃犯
中東男人是重點搜尋對象
我把報道的內容簡略地告訴了波拉特:司法部正在嚴厲打擊那些違反驅逐令的人。
「我支持它這麼做。」波拉特說。「總是有簽證過了期的人還在這兒,政府卻不管,這樣那些人就可以做壞事了。」下一句他用了英文:「太多自由了(Too much freedom)。」他緩緩地說,接著又說起了中文。「種族應該是沒有關係的;如果人們來到這兒,又遵守法律,就應該讓他們留在這兒。」
我問波拉特,他的生日午餐想吃些什麼。他告訴我,有一家伊朗餐廳做的烤羊肉串很棒,和新疆的味道一樣。我們開車經過了西蒙·玻利瓦爾德雕像,經過了世界銀行,又經過了賓夕法尼亞大道。找地方停車、停車、還是停車。找停車位的時候,波拉特對我說,他在華盛頓的生活肯定會越來越容易的。「我只是需要勇氣。」他說。「我在北京時就很有勇氣,這就是我在那兒賺了很多錢的原因。我當時需要勇氣離開。」
他在一輛黑色的雷克薩斯後面停了一會兒,看它是不是要走。但那輛車沒有動,我們繼續往前開。「我看著這兒的人們,他們很多人都沒有我聰明。」波拉特說。「有些沒有受過教育,有些年紀更大。不是說美國的所有人都是很有才智的。但,你看,很多不太聰明的人仍然可以有很好的生活。我想,如果他們能有很好的生活,為什麼我不可以呢?」
又過了幾分鐘,波拉特終於找到了一個停車位,我們下車往那家餐廳走去。餐廳的名字叫做「莫比迪克肉串屋」(Moby Dick House of Kabob)。我們走進餐廳時,波拉特微笑著揮手。另一個維吾爾族人正站在櫃檯後面烤肉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