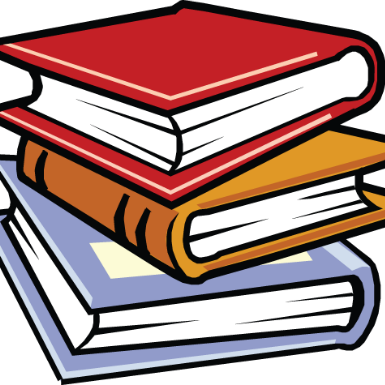一晃五年過去了。
一個秋陽如金的午後,一頂轎子進了東圈門大街,在一座高大破敗的門樓前停下。轎夫壓轎,掀簾,芝芝牽著六歲的兒子元元從轎裡出來。
芝芝玉色旗袍,藍緞背心,臉上粉黛薄施,釵環簡易,整個流露的是一種山居鄉野的純樸氣息,與繁華競奢的揚州城相去甚遠。
因是一頂平平常常很不起眼的小轎,因此沒有引起任何人注意,本來安安靜靜的街上仍然安安靜靜。芝芝付了轎錢,牽著元元慢慢往前走。抬眼望,兩邊森森然儘是青灰色水磨到頂的高牆,長期的風侵雨濕,磚頭風化脫落,牆面凸凹不平,高處不時顯出一個個結滿紅銹的鐵巴鋦。芝芝手摸著牆,轉臉道:「元元,這就是你公公家以前的院子。」
元元仰起小臉:「公公家房子這麼高?這麼大?」
芝芝點頭。
大門兩邊高大的漢白玉石鼓上蒙了一層灰,遠遠失去原先的氣勢。門樓上,磚雕,斗拱,撐牙,飛翹的簷角,一切倒還是當年的樣子,只是門頭下空空蕩蕩,不見了原先的匾額。門還是兩扇黑漆大門,一扇合著,一扇開著,油漆斑駁,露出木頭的本色。
門裡好像有人,有聲音隱隱傳出。芝芝想進去看看,又怕冒昧,見東南角御碑亭旁有一個擺燒餅攤子的老人,牽著元元過去,賣了兩塊燒餅,一邊站著吃,一邊與老人搭話:「請問大爺,那邊是原來的康府嗎?」
老人雙手揉面,望望她:「不錯,是原來的康府,可它換了門庭啦。」
「換成哪家啦?」
「汪家。」
「汪家幹什麼的?」
「也是鹽商,大發啦,跟當年康老太爺一樣,腰纏萬貫呀。」
「您老人家也曉得康老太爺?」
老人將一塊粘滿芝麻的燒餅貼入草爐:「怎麼不曉得?全揚州城個個曉得。康老太爺,康商總,頭號大戶呀。當年這運河上來來去去的鹽船,一半都是他家的,府上光園子就有好幾個,個個宮殿似的。乾隆爺下揚州,親自給他封爵送銀兩,還到他府上喝酒做詩,把個揚州城都紅透啦!可萬萬想不到,到後來竟犯了案,乾隆爺也不搭救,先是坐牢,然後回老家病死啦。命呀。」
芝芝沉默。停了停問:「聽說康府的下人,有的後來發跡了,有這回事嗎?」
「有,有。」老人在凳子上坐下,點起一鍋子煙,「那個翟大管家最是大發了,他有個小奶奶,住在鵝頸巷,常讓丫環到我攤子上買燒餅,喜歡吃我的草爐燒餅,翟大管家把她帶到金陵,手裡又是金店,又是當鋪,開了好幾爿,日子過得很是滋潤。還有個在鹽號管事的小伙子,叫小昌子,八面玲瓏,神氣活現,帶著康二爺丟下的一個奶奶,據說這個奶奶從前是春香樓的頭牌,去淮安做起鹽商,生意很大。倒霉的是康老太爺的幾房兒呀媳呀,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四處逃難。最可憐的是北府的一個奶奶,早先康二爺為討她的喜,曾在觀音山頂上撒了幾萬兩銀子的金箔,康家敗落後,被緝私營的馬管帶相中,一心要抬回去做妾,哪曉得這個奶奶是個烈性,硬是不從,上吊死了。活作孽呀!」
芝芝與老人告別,牽著元元向大門走去。
門開著,門檻沒有卸掉,很高,元元執緊媽媽的手,腿抬得高高,身子整個歪過來才跨進去。
有兩個工匠在裡面拖尺丈量,見進來一位少婦,停住手,恭恭敬敬施禮:「少奶奶好!」
芝芝知道他們把她當汪家媳婦了,含笑還禮。
從福祠前走過,進儀門,芝芝來到喜字大院。芝芝當年在揚州,跟姐姐就住在這個院。
院裡的路好長時間沒人走了,路面上落滿了樹葉鳥糞,這裡那裡的磚塊瓦礫間冒出一蓬蓬綠草,高及膝蓋,背陰處的石板上生出青苔,蒼碧冷翠,屋頂瓦行裡的瓦稜草,枯黃的草稈在秋光裡搖曳。一直往前走,一帶粉牆,秋桂軒的花瓶門出現在眼前。門上掛著鎖,壞散了,銹跡斑斑。透過花窗,可以看到天井南面的花園,特別是迎門而立的兩棵樹:一棵女貞,一棵石榴。芝芝清楚地記得,當年在這兩樹之間扎過一架鞦韆,她與姐姐坐在上面由丫環推著,蕩過來,蕩過去,蕩過來,蕩過去,好開心。透過雜亂的樹影再往前,芝芝看到了船形琴房,那裡朝東有一溜紅木格子大玻璃窗,很清雅,很灑脫。當年姐姐經常待在這裡,看書,彈琴,芝芝在揚州時,常跟姐姐坐在這說話。芝芝久久盯著那兒,依稀看到了姐姐的身影,一縷悠揚的琴聲悠然飄出
從琴房出來,芝芝走進父親與藍姨住過的壽字大院。
走進穿堂,當年迎面而立的那架金絲楠木大插屏沒有了,大堂裡整個暗昏昏,空蕩蕩,灰濛濛。從後面屏門出來,經過天井,再往後走不通了,迎面厚德堂的門鎖上了。芝芝在門前站了站,想到父親居家時喜歡在這裡喝茶,與清客談笑,每有要客臨門,都在這裡接待。芝芝特別忘不了的是,為了自己的婚事,父親在這裡對她發的那陣火。
芝芝又去了大哥的祿字院和三哥的福字院。很可惜,都鎖著進不去,只能透過花窗朝裡望望。
沿火巷一直往後,這就到了康府當年的後花園。後花園的門歪倒在地,芝芝牽著元元的手往裡走,腳下小心地讓著倒在地上的爛門板。
整個成了一座廢園。假山坍塌了許多,破碎下來的石頭散散落落,有的成了一片片,有的甚至成了粉狀。高崖上,青籐長瘋了,橫七豎八披下來,瘋女人的頭髮似的。曲橋的紅欄油漆脫盡,木頭變黑了,發爛了,走在上面搖搖晃晃。碰鼻碰眼的老樹,枝柯橫斜,遮天蔽日。黃葉飄飄,不時打到頭臉,路面上落了厚厚一層,腳踩在上面「蘇蘇」作響。一陣風刮過,無數葉子飄飛打轉,落向山坡,落向池塘。池塘裡,寒水自碧,淒清寂寥。瓊花林裡驚起一隻鳥,「咕呱呱——」撲稜著翅膀鑽向青空。
元元的小手一下攥緊芝芝的手。
「是老鴉,不怕。」芝芝說。
元元緊貼著媽媽,小臉白灰灰。
就在這時,「呀呀呀」一陣怪叫,一個白髮白鬚的瘋子手舞鋤頭從竹林裡衝出,頭髮髒亂,滿頭草屑,髒兮兮的臉上左一道右一道儘是劃破的血痕,兩隻白眼透過亂髮向前瞪著,衝到跟前,鋤柄一橫,兩隻髒手沖芝芝飛速暴烈地做著手勢。芝芝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這是康老爺的園子,不許你們收!不許!
芝芝眼淚一下湧出。
這是花大叔呀!他怎麼還在這裡?他怎麼變成這樣?
芝芝見他急,連忙向他做手勢:我不是來收園子的,我只是過來看看,只是看看。
老人漸漸安靜下來,僵硬的目光一點一點變得柔和。芝芝將整個臉對著他,希望他認出自己。可是芝芝發現,他的目光石頭一般,灰冷,僵硬,沒有一絲一毫光亮。
突然,老人咧開嘴,臉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嘴裡「呀呀」叫喚,兩手激動地做起手勢:
老爺明天回來!菩薩告訴我的!我曉得!老爺明天回來啦!明天回來啦!
芝芝對他默默點頭。
老人繼續手勢:不像話呀,院牆塌了,跟他們一趟一趟說,就是不管,就是不修,敗家精呀!老爺回來一定饒不了他們!都打板子!打板子!打!打!屁股打爛了老人滿臉紅赤,一頭大汗。
芝芝不想讓眼淚流下來,牽著元元,默默從廢園出來。
第二天上午,芝芝來到甘泉山腳下的碧雲庵。一個青衣老尼雙手合十,道一聲「阿彌陀佛」,引她進門。
沿著碎磚甬道向前,迎面一片雜樹叢,轉過樹叢上台階,芝芝遠遠看到一個青衣小帽的尼姑從庵堂走出。芝芝吃一驚,雙腳收住。
是她!不錯,真的是她!
對方感覺到有人盯她,微微俯首,雙手合十,小步向前急走。
芝芝輕叫:「藍姨!」
芝芝又叫:「藍姨,我是芝芝!」
對方頭越發低得深,腳步趨急。
芝芝定定地望住她,嘴張了張。
身影飄忽,一轉眼,在樹叢後消失。
跋
我一直覺得,生在揚州是一件很幸運的事。一次陪外地一位詩友在揚州轉園子,晚上小酌,詩友無限感慨道:「揚州公園這麼多,隨便捧一個到我們那兒都是寶,你生活在這裡,老天爺真是太厚愛你了!」
言之鑿鑿。
歷史上揚州的富庶繁華與鹽關係至密。記得小時候常到父親的廠裡玩。廠在揚州引市街邊,靠古運河,是一條老街。石板路,很深很長,兩邊都是青牆黛瓦馬頭牆,許多門頭上都有水磨磚雕飾,門口立著石鼓子,很是威武氣派。我好奇,揣著幾份恭肅往裡走,一路輕腳慢步,頗有點「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的狀態。後來聽父親說,「引市街」的「引」,是「鹽引」之義,這裡在清代聚集著大大小小很多鹽商,他們在這裡買賣鹽引,做鹽的生意,熱鬧得很。
之後書讀多了慢慢知道,在揚州,由鹽浸潤發育的不僅僅是一條街,還有一家家書院,一座座寺廟,一片片園林可以說,清代揚州鹽商如同太陽,其熾熱而燦爛的光輝輻射了整個揚州城,使得當時這裡一切的一切,大至城池市井、商業文化,小至一樓一橋、一草一木,無不折射著它的光焰與色澤,從而發出幸福的歌吟。
生於揚州又深愛揚州,積年累月裡,一回首,一顧盼,觸及的總是先輩們留下的遺跡,於是不免情思恍惚,時不時幽思冥想:揚州鹽商——這個曾經令大清帝國仰視了四百年的商業寡頭,他們憑借怎樣的秘訣積聚出無比龐大的商業資本?他們的驕奢淫逸達到了怎樣登峰造極的境地?他們龐大的商業資本,為什麼不能像大英帝國那樣催生出蒸汽機與產業革命的赤子,只是一味地奢侈、糜爛、腐化、逸樂,並對後世產生若干負面影響?鼎盛時期的他們,烈火烹油,炙手可熱,一旦轟然倒塌,何以家抄籍沒,父囚子亡?天意乎?人禍乎?在他們身上隱匿著怎樣人性的秘密?最終的悲劇對今人又有著怎樣的警醒和啟迪?作為寫作者的我,於是深埋在心底裡的一粒種子萌發了:寫一本鹽商小說,好好表現一下我們的先人,讓天下人知道他們當年輝煌的生活。
這是一部歷史小說。為了寫它,我進行了一番「惡補」,暴食性地閱讀了一批以往較少涉足的書籍:《中國鹽業史》、《兩淮鹽法志》、《揚州畫舫錄》、《清代六部成語詞典》、《中國古建築學概述》、《兩淮鹽商》、《南巡秘記》、《水窗春囈》、《履園叢話》、《陶庵夢憶》、《揚州古港史》、《清代野史大觀》等。但創作的規律告訴我,真正優秀的文學典型,往往臉在山東,眼在山西,嘴在廣東,衣服在浙江,是一種多面體的藝術糅合。史料之於我,只是為了形成飛翔的翅膀,而不是讓它食而不化地堆積在心中,限制甚至阻礙藝術翅膀的高飛。為此,我甚至將不同時態的人物、不同空間的事件拉扯到一起,令它們開花結果。有時還改變一些歷史上的稱謂,比如揚州瘦西湖在乾隆時叫保障湖,五亭橋叫蓮花橋,小說中卻一律採用今人的叫法。此外還把當時還沒有後來才相繼出現的個園、富春、共和春、煙花醉等園林飯店與酒的名稱聚入小說,目的是為了讓一個外鄉人進入我的家鄉揚州後,更便捷地認識她,記住她,並在胸中滋生出愛意。我之所以如此喋喋不休,實在是希望這種融會變通的做法,不致遭受極少數有考證癖的先生們的詬病。
寫這本小說,我用了將近兩年時間。那兩年的時光,是我生命中的節日,每天載歌載舞,若癲若狂,情感與思想如春草一般瘋長,眼前永遠是「奼紫嫣紅開遍」。
也有累的時候,也有僵木枯澀的狀態,這時騎一部單車,去個園、荷園、汪氏小苑溜溜,或者去引市街、綵衣街、南河下轉轉。霜風雪霽,夕陽晚照,一個人徜徉在深巷之中,目光像一把曲尺不時從一道門、一扇窗、一面花牆伸進去,曲曲折折在裡面逡巡,丈量。風移影動,我分明聽到了清麗的巧笑,環珮的叮噹,看到了小姐太太們飄然如夏荷的裙裾,於是我茅塞頓開,眼前靈動出一片鮮活如桃林的生活圖畫。
真正純粹的寫作是醉人的,它是對生命的思考及其表述的一種特殊方式,整個過程美麗芬芳,與一朵花開放的過程極其相似。花開過了,自然會結出果子,果子是大是小,是甜是酸,樹不知而天知人知,天者遙不可及,可及者唯身邊的食果人,因此奉獻果子的我,竭誠盼望讀者諸君不吝賜教。
作者
2010年6月於古城揚州